论语全文注释及翻译(论语全文及译文读解)

《论语》《孟子》是我从小熟读的书。当时我祖父教我的只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一则我年纪幼小,二则祖父也不大给我讲解;只囫囵地照本反覆地诵读,以至虽能背得出来,偶然看看朱注,却似懂非懂。陶渊明的“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是不肯、不愿甚至不屑于求甚解,是对当时政局和社会风气的反抗。我却是限于主、客观条件不能求甚解。前者是出于存心,后者是出于幼稚。
到专习中国古书时候,逐渐地能主动阅读不少有关书籍,便以探求原书本意为己志。我曾得到程树德的《论语集释》,这是作者在他重病卧床六年(1933年冬到1939年8月)中集中精力所作,征引书达六百八十种之多,三大厚册,字数以百万计,搜集古今人对《论语》的解释相当完备。可惜排印错误太多,字小,而且流传不广,因为是敌伪时期华北伪政府所印,稿本后来虽已由中华书局收藏,却再没有印行。这样繁冗的书,一般人也难得有耐心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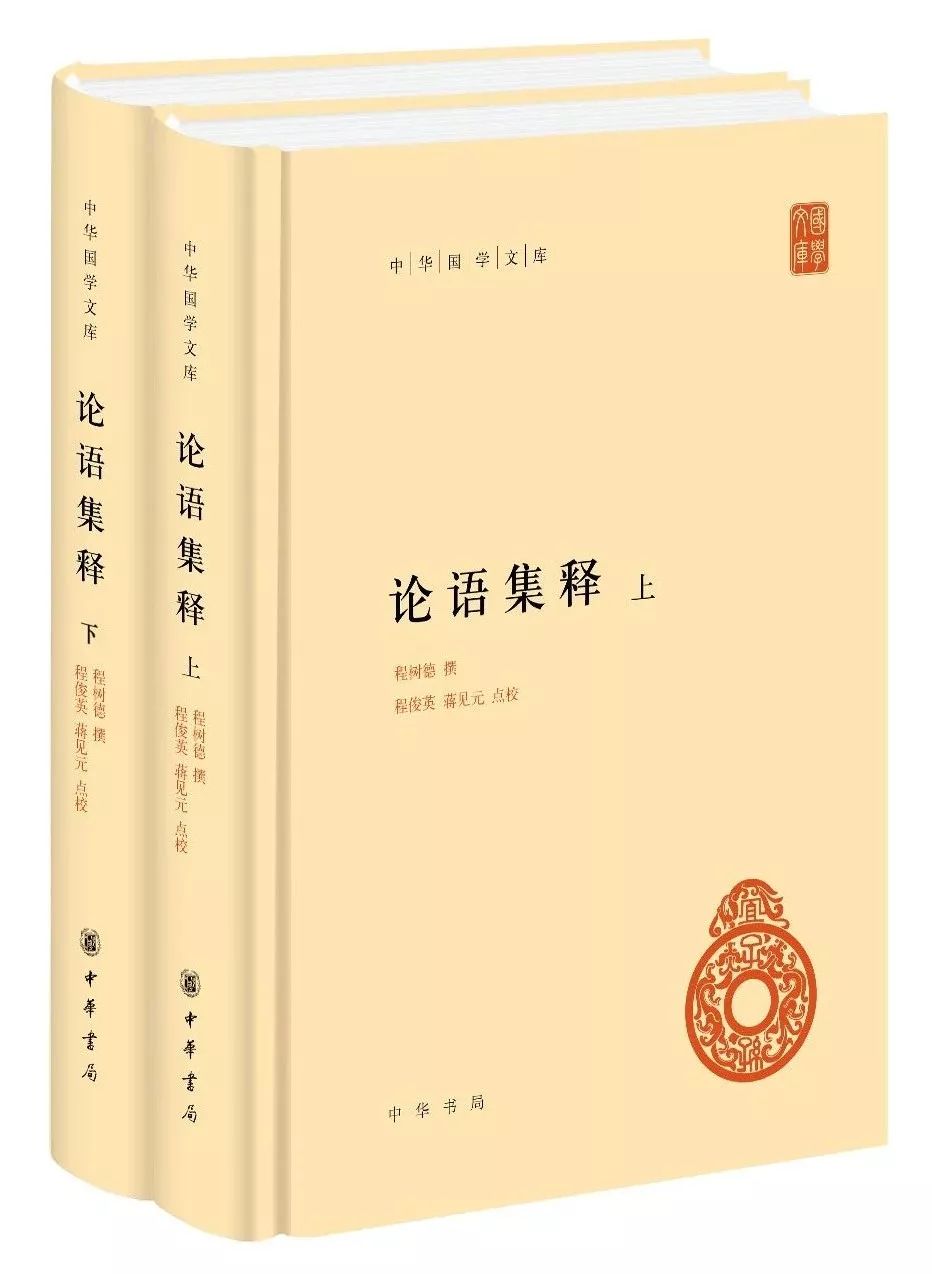
《论语集释——中华国学文库》
我读了一遍,知道《论语》每一句无不有几种讲解,到底谁是谁非,本书很少判断,因此产生一个念头,若在纷乱众说之中,采取最接近原意的加以注解并译成现代汉语,岂不有益于今日青年?
《论语》是孔子和孔门弟子言行的纪录,孔子这人是否值得宣扬,先得考虑。我本来对孔子怀着相当的尊敬,又加以阅读有关史料和评论,别的不论,我认为至少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比任何古人都巨大的。
第一,在孔子以前,古代文献都由公家掌握,因之文化知识也由贵族垄断。民间既没有教师,也没有书籍(古人叫“简策”)。孔子虽系贵族的没落者,却能得到公家所藏简策,不但学习,而且整理,并教给学生。
第二,孔子以前,只有官学,《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有“乡校”,便是郑国的国立学校,入学的都是贵族子弟,他们才能评论当时政治人物和措施。一般老百姓便没有学校可进,自然也没有老师可从。孔子则是中国第一位开办私学的人。他所招收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一般自由民,仅有极少几个贵族子弟。只要送他一点薄礼,便可列入门墙。由此可以推论,由官学向私学转化,由公家垄断的书册转到民间,才能有春秋末期到战国的文化勃兴,诸子百家争鸣。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庄子是对儒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人,但《庄子·天下篇》有下面一段话:其明而在数度(礼乐制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孔子孟子之徒)搢绅(儒服)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孔子讲学图
这话十分明白,简单地说:先有儒士,然后才有“百家之学。”由此又可以推出两条结论,一是曾经孔子学习、传授的古代典籍,后代才有传人,有比较完整的传本。今天的《诗经》《尚书》《周易》(仅《卦辞》《爻辞》二部分)《春秋》是孔子整理并传授下来的。至于《左传》所引的《志》(如文公二年引《周志》,宣公十二年引《军志》,更多的是单称《志》),都是孔子以前的古书,孔子或者无意,或者无暇加以整理和传授,便都丧失,只剩下被引用的少数语句。
又一是现今号称孔子以前的古书,如《管子》《晏子春秋》都是孔子以后人所托,前人早有定论。可以说,今日所传私人著作,没有早于孔子以前的。若讲中国文化史,孔子自是承先启后的第一人。由此之故,孔门弟子也受尊重。自西汉以至清末,《论语》便是士子的必读书。今天要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也必须以《论语》为根据,为准绳。这是我写《论语译注》主要动机。
要写《论语译注》,必须先深入了解《论语》本书的体例、词汇、语法,就是每词每句在当时的本义。我看了某些人搞的古书译注本,并没有下大功夫,其中较好的不过就他的水平依字面翻译,并不考作者的本意和本义,未免把译注看得太容易了。
我喜欢晋人陆机的一句话:“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昭明文选·文赋序》)我认为无论读什么书,必先探求作者的“用心”,才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若要得作者的用心,一定先求当时语句的流行意义,因此我在着手译注《论语》之前,先写了《论语词典》,这样,不致被纷歧的解释所迷惑。

陆机画像
譬如《为政篇第十六章》“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句,虽只八个字,却“诸说纷纭,莫衷一是”(程树德《集释》案语)。歧义之所以产生,最大关键在于“攻”字意义的确定。何晏《论语集解》说:“攻,治也。”黄侃《论语义疏》说:“攻,治也。古人谓学为治。”朱熹《论语集注》引范氏曰:“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这几家以至另外许多家都把“攻”解为“治”。“治”不仅是学习研究,也包括实行、传播。孙奕《示儿编》却说:“‘攻’如‘攻人之恶’之‘攻’。”这一说不始于赵宋,南朝任昉作《王文宪公集序》曾说过:“攻乎异端,插图归之正义。”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也说:“《周书》设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将“攻”字改作“恶”字,也是和攻伐解相近。其后清末民初的王闿运作《论语训》也说:“攻犹伐也。”(但他释这句的整个旨意却错了。)
次要关键的词是“已”字,“已”字旧有三说,孙奕说:“已,止也。谓攻其异端,使吾道明,则异端之害人者自止。”程树德却说“‘已’者语辞,不训为‘止’。”而《晋书·索传》说:“攻乎异端,戒在害己。”似乎把“已”字误认为“自己”的“己”字。至于“异端”,尤其有不同解释,自然不是孟子时代的杨朱墨翟之说,也不是韩愈时代的佛老和和尚道士。有人认为是老聃之说,那是误认为老聃在孔子前,至少今天所传《老子》的著作和流行是在孔子和《论语》以后。我研究了《论语》的词法和句法,采取了孙奕的说法。
写《论语译注》时候,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是一九五五、五六年,正值重视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时候,若向图书馆借书,只要开一书单,图书馆便派人送到家。这的确对研究工作者给予极大的方便,是具体地支持研究工作。但我被划为右派以后,被批判时,却成了罪名之一。说是借图书馆的书,隔不久便一车车(平板三轮)地送到家,一摞摞地送上楼(我住三楼)。这是图书馆在履行职责和规定,罪名却加在我头上。自然,那时是不容说理的。黑云未必能压城,功劳(或者说苦劳罢)却变成罪过。幸而这时我早完稿交给中华书局了,不然便很难继续写下去。
我在中文系被批倒批臭后,临时被安排在历史系教了一段时间《史记》。暑假后接到通知,调到兰州大学中文系,可以说是去“效力”罢。中华书局接到我《论语译注》清稿后,交童第德先生审查并任责任编辑。童先生颇有中国学者的旧风度,认真而踏实,我后来到中华书局和他共事,相处甚得。这部书是我到兰州以后才出版的,当时,出右派分子的著作,自是大胆!金灿然同志(中华书局总经理总编辑)也因此受了批评。

金灿然
但我并不因“有罪”而停笔。我还继续写《孟子译注》。当时中华书局派人到兰州大学组稿,不晓得哪一方是出谋划策者,商定压我拿出《孟子译注》全部稿件。我以戴罪之身,哪里敢有二话,况且我已经忧患受创不小,更不存名利思想,不但乖乖地,而且毫无可惜之心将所有《孟子译注》稿本交出。兰大中文系便组织若干师生讨论,据参加讨论的几位告诉我,讨论中七嘴八舌,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几乎无法定稿。有人主张用举手方式表决,以多数定是非,但进行了一段,觉得不妥。最后还是交给我,让我全权裁定。我看了他们对我原稿的修改和他们讨论纪录,啼笑皆非,却不敢、也不想露之于形色,耐心地默默地又把原稿恢复本来面目。
但第一次出版的《孟子译注》译注者是“兰州大学中文系孟子译注小组”。自然一切有关人士都分得若干元稿费(有人告诉我,他举了一次手,分得七十元),我被认为是“审定”者罢,也喝了一口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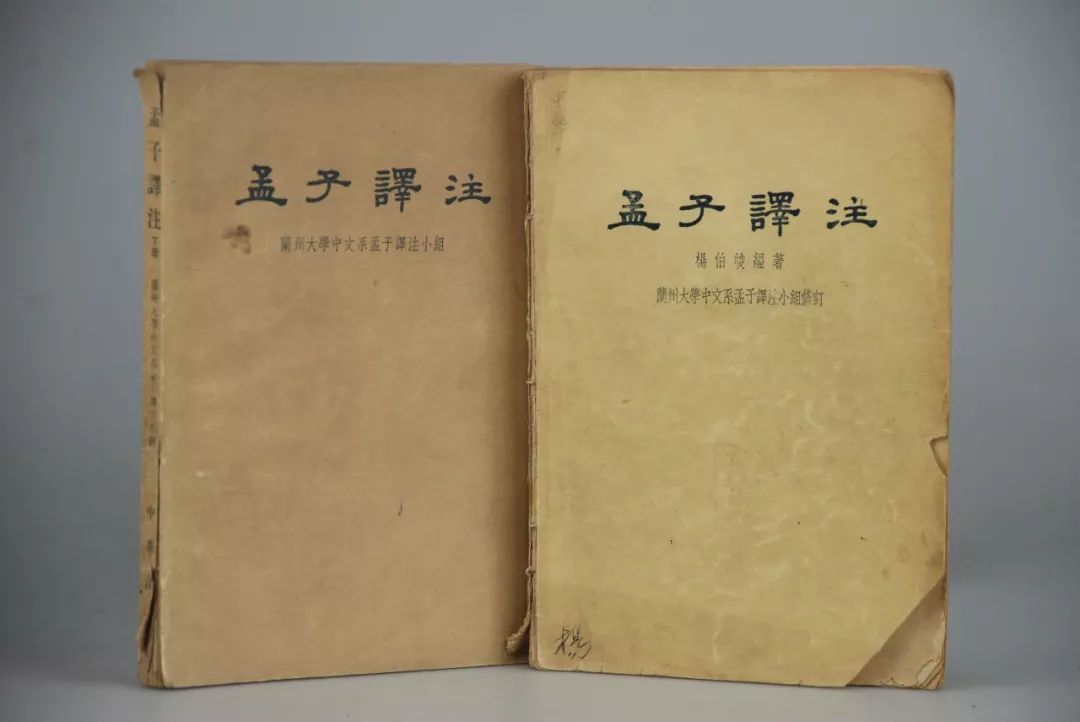
《孟子译注》署名方式的变化
我在兰州时间不到三年,忽然接到通知,调我回北京,到中华书局报到。兰州有人说:“有大学教授不当,却调到书局去卖书!”以为我再度被“贬谪”,这些人是对中华书局不了解,我也只好心中暗笑。来到中华书局不久便有一张大字报是点我的名的。对我开了一次批判会,既没有任何事实,谈不上揭发;也没有举出任何罪证,只是空空荡荡地说我如何不老实。我当时想我又不是自己要求调来的,有什么不老实?怎么调我来的经过我事后才了解。后来我才领悟到,这是承袭了宋太祖立下的规矩,先打一百杀威棒。对新进本单位的右派,实行所谓“打威风”之谓也。我那时“戴罪立功”还来不及,何威风之有哉!
会上有人睁着眼睛说瞎话,竟大声对我吼着:“《孟子译注》是你做的吗?”我处于低头认罪的情况下,夫复何言!《孟子译注》是我做的,明眼人都知道。这书已经被人强抢了去,我不曾有怨言,更不敢吐出一句“是我做的”的言语。我才知道,在极“左”路线影响下,不摆事实,不讲道理是当时的风气,我只能“低头认罪”,默不吱声。
六一年摘除我的右派帽子。中华书局当局调了《孟子译注》的原稿,加以考查,肯定每字每句都是我的,这才和兰大中文系联系,主张改用我的名字重印。兰大中文系竟然不同意,却说重印区区稿酬可以由我一人独得,译注者名义仍归兰大小组,真是可笑之至。中华书局当局这次实事求是,重印时改用我的名字,算是物归原主,终于分清黑白,明确是非,使这部多灾多难的《孟子译注》重新和广大的读者见面。
有不少的朋友告诉我,《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是姐妹篇,不论从体制上、行文风格上看,都是出于一人手笔,所谓之译注小组竟想为图名遮掩天下耳目,是徒劳的。好在今天已是云开日朗,以前搞“群众运动”的做法,也一去不复返了。我深深地体会到,今日的中国比以前大不相同,但还得继续普及并且提高文化(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水平,政治上更加开放,有在宪法范围内的高度民主和自由,那么,出现生动活泼的局面才不是一句修饰门面的自欺欺人之谈。
(本文原载《守正出新——中华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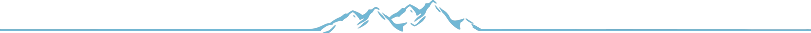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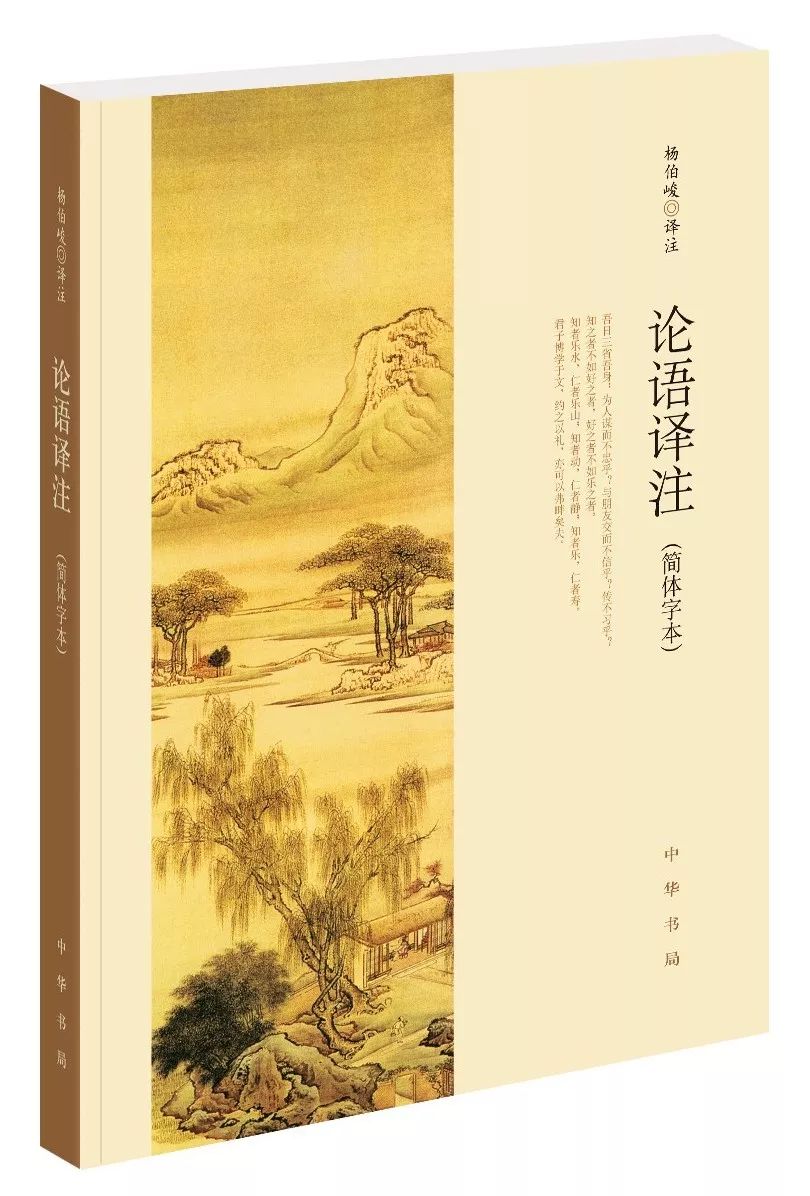
《论语译注》(简体字本)
杨伯峻 译注
简体横排
32开 平装
9787101127867
26.00元
本书系名家力作,杨伯峻先生在精研《论语》的基础上,对《论语》二十篇进行了精确细致的注释和翻译。每章分为原文、注释、译文三部分,注释精准,译文流畅明白,不但给专业研究者提供了若干研究线索,更便于普通读者正确理解《论语》,实为雅俗共赏之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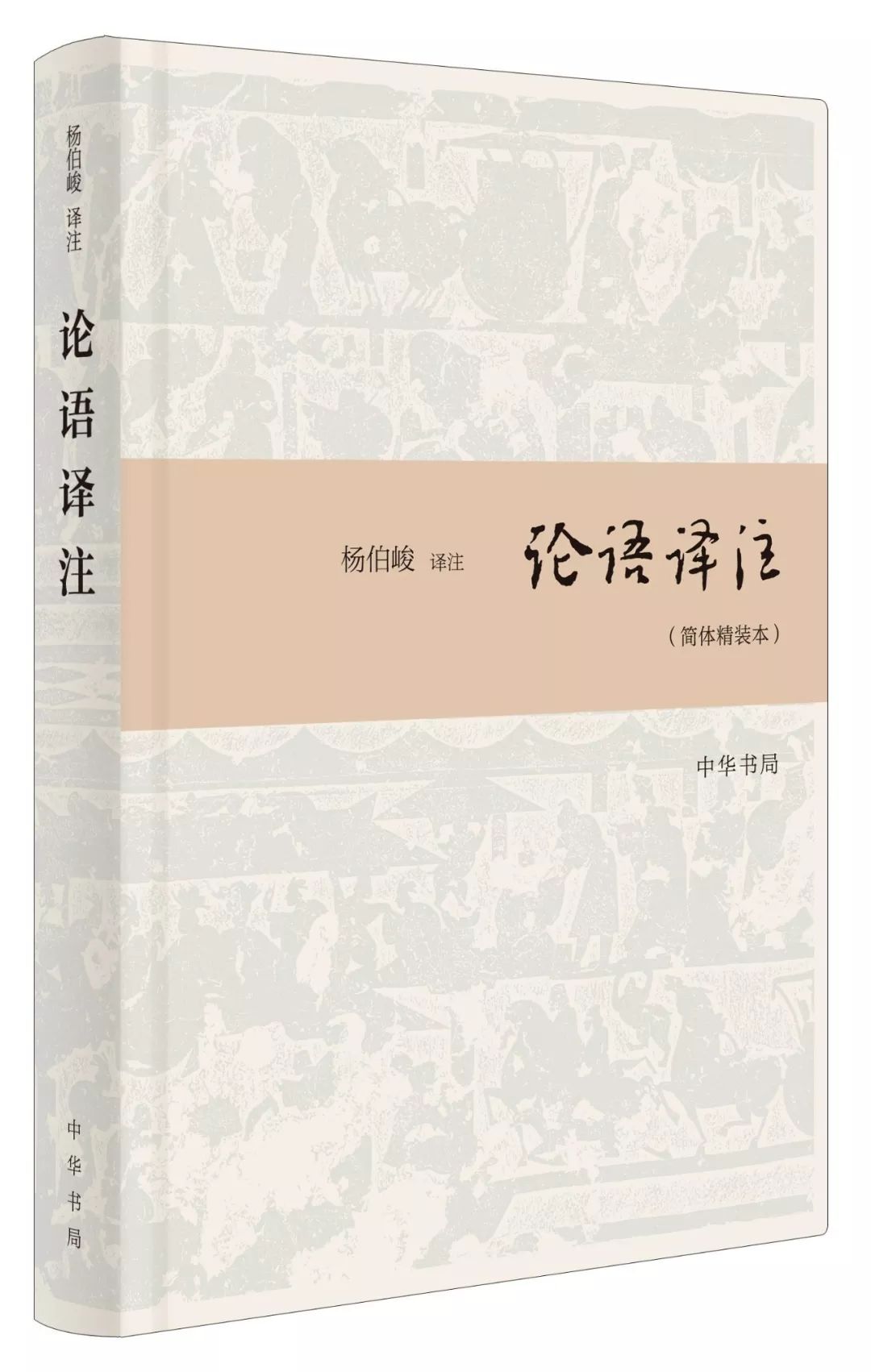
《论语译注》(简体精装本)
杨伯峻 译注
简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35763
39.00元
《论语译注》是久负盛名的名家力作,是阅读《论语》的必读之选。此次精装印制,典雅大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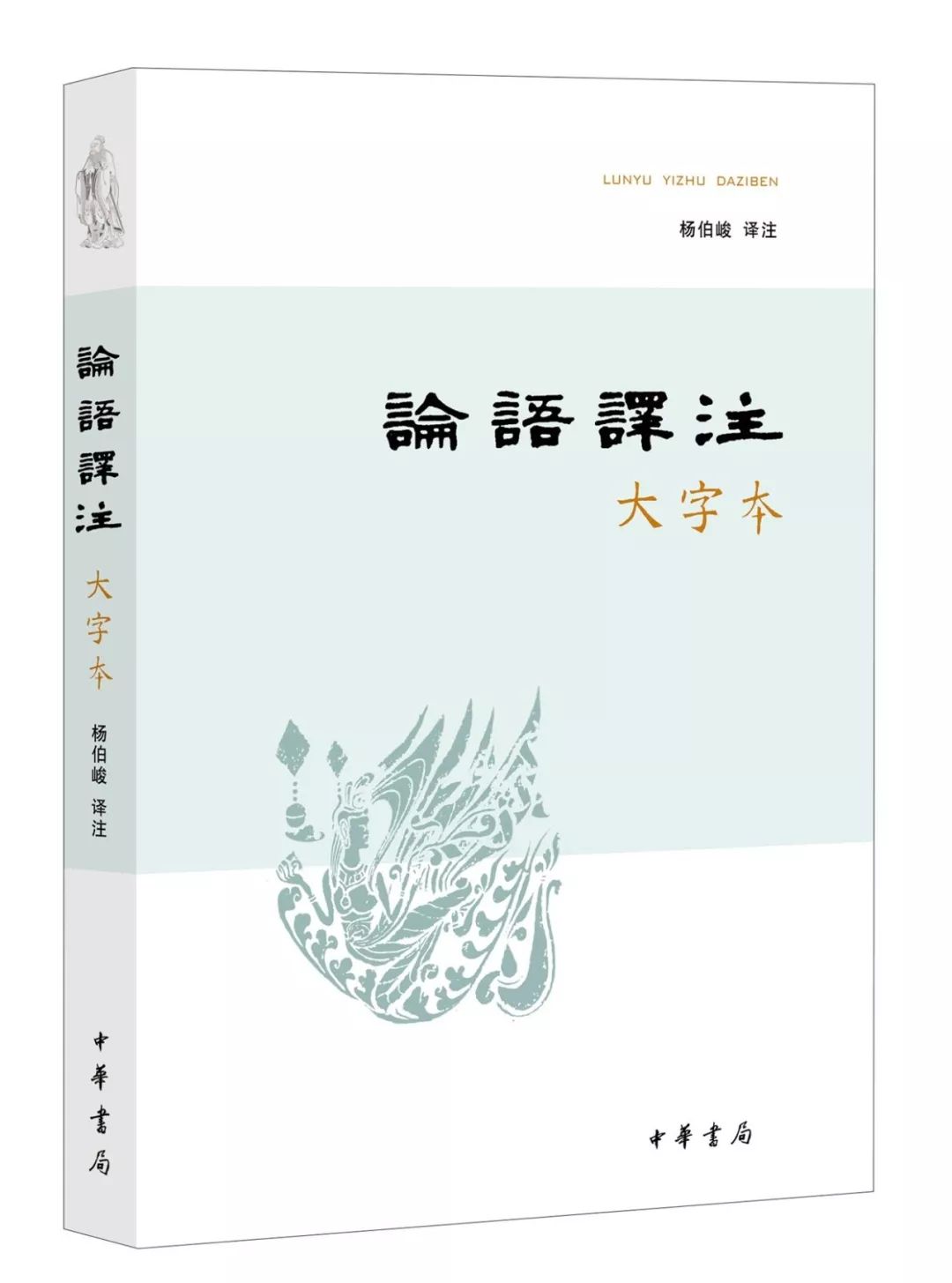
《论语译注》(大字本)
杨伯峻 译注
16开 平装
简体横排
9787101107203
48.00元
本书为简体大字本,加大开本及字号,版式疏朗,双色印刷,原文、译文及注释三部分层次清晰、重点突出,可以有效减轻视力负担,并使阅读过程赏心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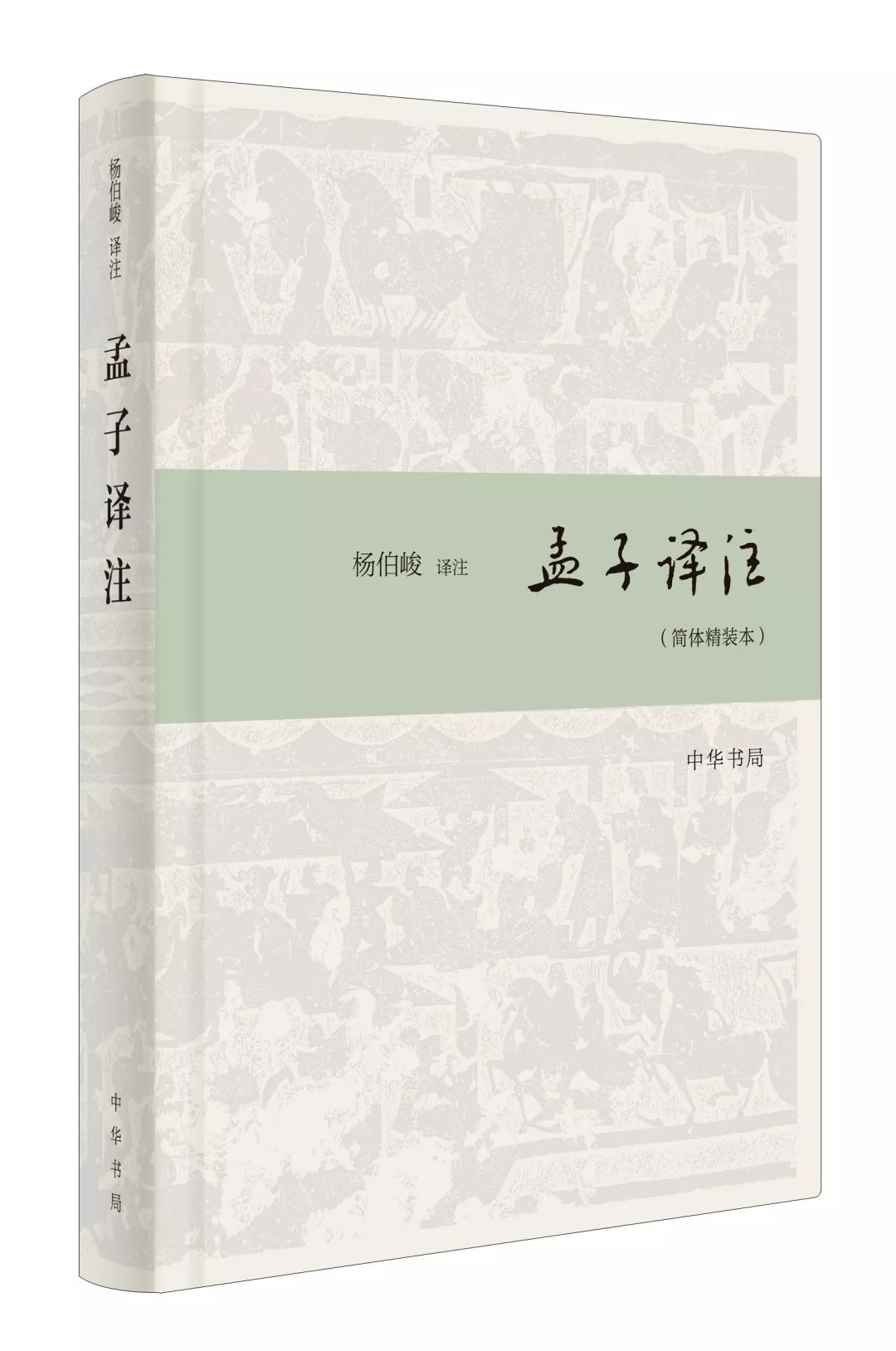
《孟子译注》(简体精装本)
杨伯峻 译注
简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35770
48.00元
《孟子》记载了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是儒家基本经典,影响极大,古往今来,注家众多。杨伯峻先生的译注注释准确,译注平实,脍炙人口,是当代最好的《孟子》读本之一,不但能帮助一般读者读懂《孟子》一书,还能给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和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