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鲁迅先生原文(伤逝鲁迅先生原文赏析)
1914年,上海春柳社将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带到中国,其中女主角娜拉那句著名的台词:
“首先我是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一个人”,令当时无数被物化的中国女性独立意识开始觉醒。
“中国永远不缺看热闹的人”,很多人热切地效仿娜拉,盲目地以爱之名离家出走,不愿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傀儡,追求自由与平等。
不爱凑热闹的鲁迅先生早已洞察到娜拉走进现实要面对什么生活,他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预见:“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有了透彻的思考,他笔下的“纯爱”也多了些现实的味道,《伤逝》的女主角子君,就如同走进现实的娜拉,为自由选择了爱情,但又被生活粉碎了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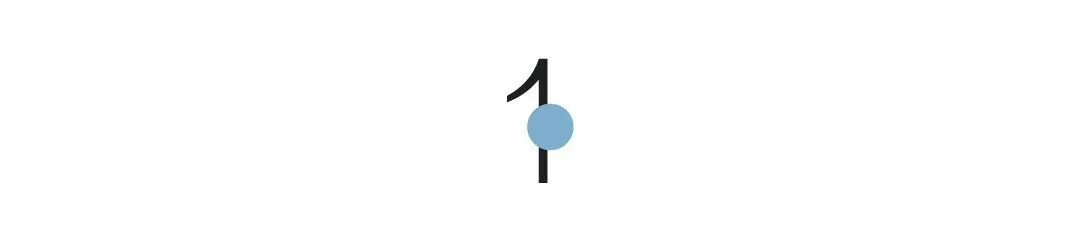
冲动的爱情,是一场抛弃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遇到涓生后,子君义无反顾地说下这句话。
他们的爱情始于一场遇见。
无意间的一次做客,百无聊赖的一次等待,涓生便听见外面高跟鞋尖触着砖路的清响。他刚刚抬起头,窗边已闪进一张生动的面庞:白皙的圆脸带着浅浅的笑窝。
随后,那人走了进来,正是子君。
她身材纤细,穿着条纹布衫,玄色裙子,手里捧着紫白的藤花,安静而美好。

她常住在叔叔这里,今日不知怎的,恰巧来到客厅,于是便遇见了涓生。
一个眼神的触动,彼此似乎没什么生疏隔阂,正如宝黛初见便生一句“这个妹妹我曾经见过”的亲昵。想来,这便是心动。
可是他们都是接收了新思想的文艺青年,自不会仅仅眉目传情,暗送秋波。
默默地相视片刻之后,屋里便渐渐充满了聊天的话语,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
大多数时候,涓生在高谈阔论,子君总是微笑点头,但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那份明亮,让涓生心里一暖:她懂得。
就这样交际了半年,涓生终于向子君表示了纯真热烈的爱,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一同道出的还有他的意见,他的身世,他的缺点。
他只是一种抒发,并没打算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子君真的接受。
然而,子君义无反顾地说出了那句话,仿佛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涓生还透澈,坚强得多。
此时的涓生,太需要在他寂寞聊赖的生活里来一簇热火,为他这棵“半枯的槐树”带来“新叶”, 使他“骤然生动起来”,也“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
此时的子君,早就在等待一个足以让她证明自我觉醒的方式,为她敢于和“鲇鱼须的老东西”及脸上涂着“加厚的雪花膏”的小东西为代表的社会决裂找到出路。

依赖与欲望交织一起,便产生了冲动的爱情。
冲动的,不仅仅是思想和心灵。
为了互表衷心,子君和全然反对的家人决裂,涓生和好生劝解的朋友绝交,两个人一起为爱私奔,甘愿在这熟悉的城市里,变成无依无靠的陌生人。
私奔,大概是这世界上最大的“伪浪漫”。
表面上看,是为了爱情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但殊不知,思虑欠奉的破釜沉舟,多半都不会长久。现实的消磨多会为冲动的爱情买单。
因为当你为了爱情不留后路地抛弃所有时,身边的一切也在毫不犹豫地抛弃你,包括原本的自己。

爱情的甜,会败给生活的苦
有人说,童话故事之所以把公主和王子完美婚礼作为结局,是因为婚后的生活,和童话里的浪漫无关。
不浪漫,从私奔后匆匆寻找容身之所的那一刻,便已注定。
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大半被托辞拒绝,看了二十多处,才得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为此,涓生花费了大量积蓄,子君当掉了自己的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
搬进了属于两人的小屋,满怀着为爱新生的热情与期待。那时,涓生满怀热切地对子君说:“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 子君也领会得点点头。
然而却未料到,甜蜜的期限太短,藏在爱情这袭华美长袍下的虱子蠢蠢欲动。

“有情饮水饱”,仿佛是一个诅咒。挑战感情首当其冲的,便是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为了挣钱养家,涓生每星期有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终日坐在办公桌前抄那些公文和信件换取微薄的收入,在平庸而压抑地工作中消磨着自由与理想。
为了省钱持家,没有工作的子君日夜操心如何用最少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她包揽了一切家务,终日汗流满面,双手也粗糙起来,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
当两个人都为生活而苦的时候,自然无暇再理会心灵的对话,现实的狼藉把爱情渐渐击碎,终究,当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在涓生的眼里,子君从婚前“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中国新女性,迅速蜕变为一个只知洗衣做饭,养鸡养狗,不修边幅的旧女性。
然而,涓生的失业,对这挣扎在生存线上小家庭的打击,无疑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们先是默默地相视,商量后决定将现有的钱再竭力节省。涓生一边登“小广告”去寻求抄写和教读的工作,一边写信请求给认识的编辑收用自己的译本。
而子君在家里主要的工作变成了筹钱吃饭,斤斤计较每一寸用度。
重新找工作的日子并不算顺利,子君为生活忧虑的心却一点点加剧,这令涓生更加的心烦意乱。
逐渐地,子君养的宠物油鸡变成了菜肴,宠物狗也因为食量太大被抛弃于郊外。

油鸡和小狗曾是子君独自在家唯一的陪伴,但在一开始就只喜欢养花不喜欢养动物的涓生那里,都成了生活和精神的拖累。
这拖累里,甚至包括了子君经营的一日两人三餐四季。
“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帖了。”
“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
“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
……
物质在文艺青年的眼里远没有爱情高尚,但它的世俗偏偏能够改变人,改变生活,改变爱情。
没有事业的保障,没有家人的仰仗,没有朋友的依仗,开场再美好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走几步就散了。
在被生活的苦侵蚀的那一刻,所谓爱情被瞬间打回原形,如此不堪一击。

沉稳自爱,而后爱人
“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
涓生吃力地伪装着,忍受着,眼睁睁地看着勇敢的子君变得懦弱,骄傲的子君变得常有怨色,不畏将来的子君变得害怕未来,而他则将生活的失败归结于子君的改变:
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

抛弃掉她寂寞操劳时唯一的慰藉,家里没有了鸡飞狗跳的生气,气氛愈加冰冷。
涓生逃出了家门,大道上,公园里,最后终于在图书馆里每日栖身。
子君变了吗?
子君也许变了。
她曾经也是个不为生计烦恼的文艺女青年,涓生的出现让她渴望在自由的爱中获得滋养,于是她愿意与他私奔,哪怕面对社会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只是大无畏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但没有物质依靠和亲友祝福让她变得孤独无助,脆弱迷茫,在经济上无法独立但在感情上倾注所有的子君,除了尽力抓住当下的选择,别无他法。
子君的“新”,算是走到了终点。
子君或许也没有变。
因为现实中的涓生,不过如同困在局里的生活的禽鸟,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日子一久,只麻痹了翅膀,他是压抑的,脆弱的。
因此遇见子君后,便对她为爱果敢的悸动,赋予了追求自我价值、反抗礼教陋习、追求婚恋自由平等等“上纲上线”的过度解读。

子君成为了涓生内心自由的想象,内心怯懦的保护伞。所以在风雨来临时,他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只能将埋怨、后悔、失望全部指向子君,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爱情来得时候,涓生不曾沉稳以对,执着地把感情视为所有,无力改变化为对感情执念,对生活怨念。
爱情走得时候,子君不曾独立自爱,执着地用回忆和空虚掩饰感情的窟窿,拉扯住对方不放手,对现实视而不见。
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
又勉强维持了几个月,当子君追问时,涓生终于向子君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
没有诧异,也没有争吵,子君平静地离开,她有权选择爱情的开始,却没办法阻止它的消逝。
她无处可去,只能央父亲来接自己,没有人知道一个私奔又归家的女子回去后要遭受多少冷嘲热讽,谩骂猜忌。
原来无论在什么年代,婚姻的真相都是一样的,没有物质的爱情是都不长久,丧失自我的爱情更是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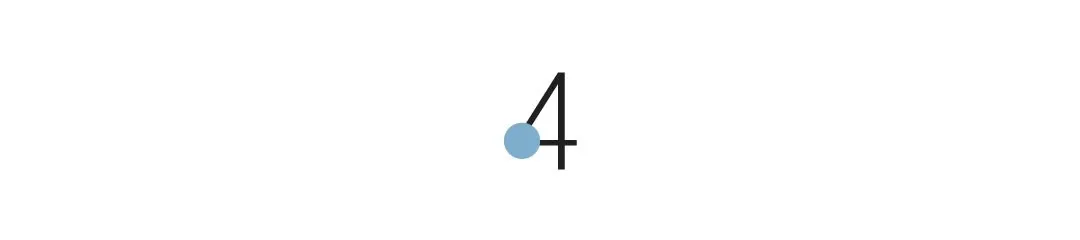
《伤逝》是鲁迅笔下唯一的爱情,这部小说的最后,勇敢追求爱情的子君,既没有获得自由,也没有收获长情,她只能用死亡,祭奠她逝去的爱情,和不堪忍受的流言蜚语。
为爱出走的是女性,走不出爱情的依旧是女性,成为爱情的牺牲品,是那个时代的女性的悲剧。
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即便面对爱情,鲁迅先生也反对盲目的爱:“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在他给许广平的信中也曾提到了他的爱情观: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爱情应该是我们深思熟虑后的某个选项,不值得飞蛾扑火的孤注一掷,有了爱情让我们变得更好,但没有爱情,我们依旧能活得很好。
掌握人生的人才能掌握爱情,才能让爱情的甜抵挡住生活的狂风暴雨或风轻云淡,这样过着,便是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