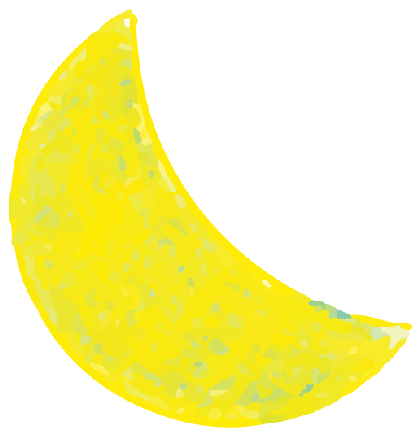赞美父爱的诗句有哪些(歌颂父爱的句子鉴赏)


父爱无言,父爱如山
他从来不说爱你,却给了你全部
他或许不曾拥抱你,却为你遮风挡雨
今天我们精选中外12首关于父亲的诗
祝愿天下所有父亲,幸福安康!

父亲和我 | 吕德安
父亲和我
并肩走着
秋雨稍歇
和前一阵雨
好像隔了多年时光
我们走在雨和雨的
间歇里
肩头清晰地靠在一起
却没有一句要说的话
我们刚从屋子里出来
所以没有一句要说的话
这是长久生活在一起
造成的
滴水的声音像折下的一条细枝条
像过冬的梅花
父亲的头发已经全白
但这近乎于一种灵魂
会使人不禁肃然起敬
依然是熟悉的街道
熟悉的人要举手致意
父亲和我都怀着难言的恩情
安详地走着

在一间小小的公寓 | (波兰)扎加耶夫斯基
我问父亲,“你整天都做什么?”“我回忆。”
那是在格里维策一间满是灰尘的小公寓房,
苏维埃式样的、低矮的街区
他们说所有的城市都应看起来像营房,
狭窄的房间便于战胜阴谋诡计,
墙上一只老式壁钟走着,不知疲倦。
他活过了39年和煦的九月,它呼啸而过的炸弹,
利沃夫的修士的花园,闪亮的
槭树、刺槐的绿叶和小鸟,
德涅斯特河上的小划子,柳枝的香气和潮湿的沙地,
一个炎热的日子你遇见的一个学习法律的女子,
乘货客车去西部的旅行,最后的边界,
68年学生们为感谢你的帮助
送来的两百朵玫瑰,
其它一些我从不清楚的小插曲,
没有成为我妈妈的一个姑娘的吻,
童年的恐惧和甜鹅莓,在我诞生前
平静的混沌里所有的形象。
你的记忆力活跃于那安静的公寓房——在沉默中,
有条不紊,你致力于瞬间恢复
你的痛苦的世纪。
(李以亮 译)

傍 晚 | 李少君
傍晚,吃饭了
我出去喊仍在林子里散步的老父亲
夜色正一点一点地渗透
黑暗如墨汁在宣纸上蔓延
我每喊一声,夜色就被推开推远一点点
喊声一停,夜色又聚集围拢了过来
我喊父亲的声音
在林子里久久回响
又在风中如波纹般荡漾开来
父亲的答应声
使夜色似乎明亮了一下

我父亲二十二岁时的照片 | (美)卡佛
十月。在这阴湿,陌生的厨房里
我端详父亲那张拘谨的年轻人的脸。
他腼腆地咧开嘴笑,一只手拎着一串
多刺的金鲈,另一只手
是一瓶嘉士伯啤酒。
穿着牛仔裤和粗棉布衬衫,他靠在
1934年的福特车的前挡泥板上。
他想给子孙摆出一副粗率而健壮的模样,
耳朵上歪着一顶旧帽子。
整整一生父亲都想要敢作敢为。
但眼睛出卖了他,还有他的手
松垮地拎着那串死鲈
和那瓶啤酒。父亲,我爱你,
但我怎么能说谢谢你?我也同样管不住我的酒,
甚至不知道到哪里去钓鱼。
(舒丹丹 译)

我读着 | 多 多
十一月的麦地里我读着我父亲
我读着他的头发
他领带的颜色,他的裤线
还有他的蹄子,被鞋带绊着
一边溜着冰,一边拉着小提琴
阴囊紧缩,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
我读到我父亲是一匹眼睛大大的马
我读到我父亲曾经短暂地离开过马群
一棵小树上挂着他的外衣
还有他的袜子,还有隐现的马群中
那些苍白的屁股,像剥去肉的
牡蛎壳内盛放的女人洗身的肥皂
我读到我父亲头油的气味
他身上的烟草味
还有他的结核,照亮了一匹马的左肺
我读到一个男孩子的疑问
从一片金色的玉米地里升起
我读到在我懂事的年龄
晾晒壳粒的红房屋顶开始下雨
种麦季节的犁下托着四条死马的腿
马皮像撑开的伞,还有散于四处的马牙
我读到一张张被时间带走的脸
我读到我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
我父亲身上的蝗虫,正独自存在下去
像一个白发理发师搂抱着一株衰老的柿子树
我读到我父亲把我重新放回到一匹马腹中去
当我就要变成伦敦雾中的一条石凳
当我的目光越过在银行大道散步的男人……

外 套 | (叙利亚)阿多尼斯
我家里有一件外套
父亲花了一生裁剪
含辛茹苦地缝线。
外套对我说:当初你睡他的草席
如同掉光了树叶的树枝
当初你在他心田
是明天的明天。
我家里有一件外套
皱巴巴地,弃置一旁
看到它,我举目打量
屋顶、泥土和石块砌成的土房
我从外套的窟窿里
瞥见他拥抱我的臂膀
还有他的心意,慈爱占据着心房
外套守护我,裹起我,让祈望布满我的行旅
让我成为青年、森林和一首歌曲。
(薛国庆 译)

给父亲 | 北 岛
在二月寒冷的早晨
橡树终有悲哀的尺寸
父亲,在你照片前
八面风保持圆桌的平静
我从童年的方向
看到的永远是你的背影
沿着通向君主的道路
你放牧乌云和羊群
雄辩的风带来洪水
胡同的逻辑深入人心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
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掌中奔流的命运
带动日月星辰运转
在男性的孤灯下
万物阴影成双
时针兄弟的斗争构成
锐角,合二为一
病雷滚进夜的医院
砸响了你的门
黎明如丑角登场
火焰为你更换床单
钟表停止之处
时间的飞镖呼啸而过
快追上那辆死亡马车吧
一条春天窃贼的小路
查访群山的财富
河流环绕歌的忧伤
标语隐藏在墙上
这世界并没多少改变:
女人转身融入夜晚
从早晨走出男人

挖 掘 |(爱尔兰)希尼
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间
一支粗壮的笔躺着,舒适自在像一支枪。
我的窗下,一个清晰而粗厉的响声
铁铲切进了砾石累累的土地:
我爹在挖土。我向下望
看到花坪间他正使劲的臀部
弯下去,伸上来,二十年来
穿过白薯垄有节奏地俯仰着,
他在挖土。
粗劣的靴子踩在铁铲上,长柄
贴着膝头的内侧有力地撬动,
他把表面一层厚土连根掀起,
把铁铲发亮的一边深深埋下去,
使新薯四散,我们捡在手中,
爱它们又凉又硬的味儿。
说真的,这老头子使铁铲的巧劲
就像他那老头子一样。
我爷爷的土纳的泥沼地
一天挖的泥炭比谁个都多。
有一次我给他送去一瓶牛奶,
用纸团松松地塞住瓶口。他直起腰喝了,马上又干
开了,
利索地把泥炭截短,切开,把土.
撩过肩,为找好泥炭,
一直向下,向下挖掘。
白薯地的冷气,潮湿泥炭地的
咯吱声、咕咕声,铁铲切进活薯根的短促声响
在我头脑中回荡。
但我可没有铁铲像他们那样去干。
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间
那支粗壮的笔躺着。
我要用它去挖掘。
(袁可嘉 译)

委 屈 |朵 渔
某年,父亲在挖树时
砸伤了腰
我连夜赶回,他
躺在小床上,动弹不得
母亲站立一旁
为他乌黑的双脚
涂药
我替他挖掉
剩余的树根,帮他的庄稼
浇水、施肥
回城前的晚上,把
剩余的钱交给母亲
让她留着慢慢使用
当时鸡已上架,月亮
也不好
一家人安静地喝汤
沉默中,渐渐传来
父亲的啜泣
这么多年来,他还是
第一次在儿子面前
流泪,那种委屈呵
简直不像个父亲

遥远的脚步 | (秘鲁)巴列霍
父亲在沉睡。威严的面孔
表明平静的心灵。
现在他多么甜蜜……
那就是我——如果他有什么苦的东西。
家中一片沉寂;人们在祈祷;
今天没有孩子们的消息。
父亲醒来,聆听
逃往埃及那依依惜别的话语。
现在他多么近啊……
那就是我——如果他有什么遥远的东西。
母亲漫步在果园,
品尝着不是滋味的心酸。
现在她多么温柔,
多么出神,多么飘逸,多么爱恋。
家中一片沉寂,没有喧闹,
没有消息,没有天真,没有稚气。
如果有什么波折在傍晓降临并瑟瑟有声,
那就是两条白色的古道,弯弯曲曲。
我的心正沿着他们走去。
(赵振江 译)

哎 呀 | 西 娃
我在飞快宰鱼
一刀下去
手指和鱼享受了,刀
相同的锋利
我“哎呀”了一声
父亲及时出现
手上拿着创可贴
我被惊醒
父亲已死去很多年
另一个世界,父亲
再也找不到我的手指
他孤零零地举着创可贴
把它贴在
我喊出的那一声“哎呀”上

我父亲的鼾声 | (美)莎朗·奥茨
深夜时分,我会听见它穿透墙壁——
我父亲打鼾,那稠密、不成调的
凝结的粘液在他鼻腔里上升着
又落下着,像一团团海藻一个波浪
卷进来又卷回去。那阻塞的咆哮
充满房屋。甚至落入厨房,
在橱柜中,刀叉随着远处的震动
发出低哼声。但在我的紧挨着
他们的房间里,它是那么响亮,
我能感觉到自己在他体内,
在他生命打结的绳索上被举起
再放下,进入狭窄的
锯齿状的井,其琥珀墙
滑动在我躯干周围,波旁酒的气味
像痰一样刺鼻。他通宵躺着
像一头被击倒的野兽,发出粗重的
被埋葬的、阻塞的呼叫,像哭喊
求救。而永远无人前来。
在周围任何地方没一个他的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