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诗八首赏析(穆旦著名的诗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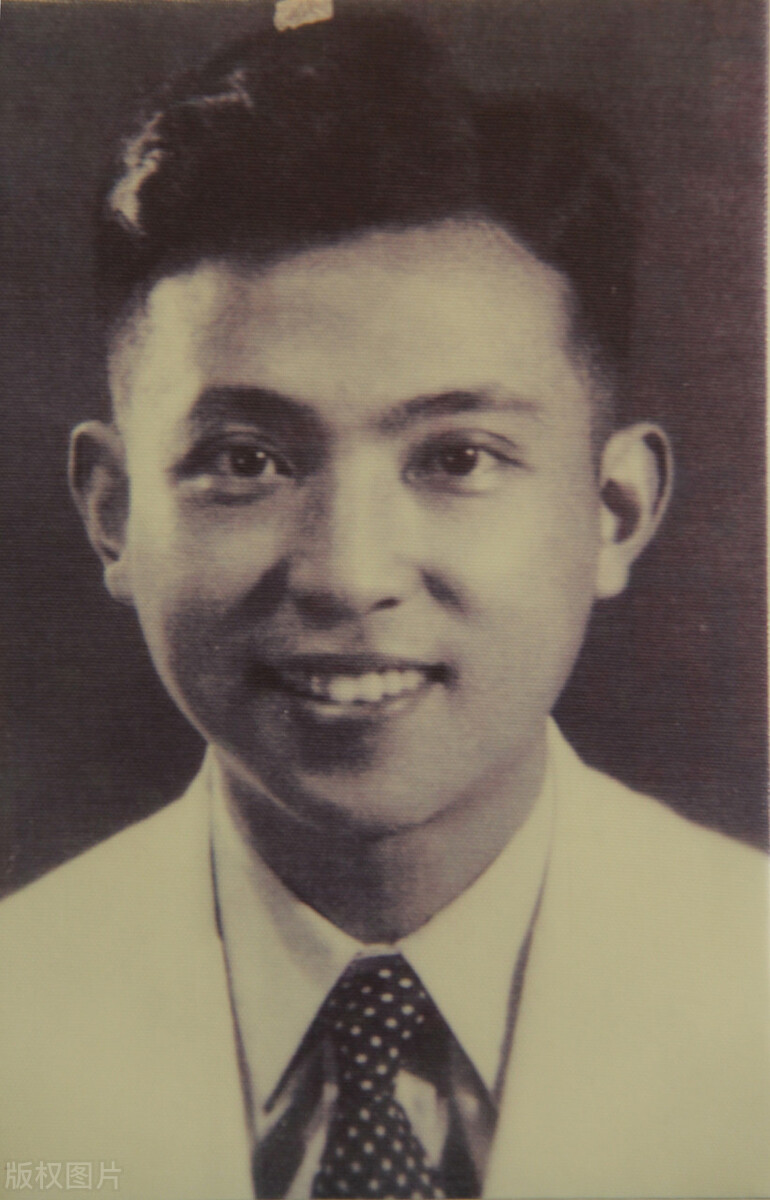
穆旦的《诗八首》(写于1942年)在写出不久(1946年)就被王佐良誉为“现代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王佐良. 一个中国诗人[M]. //穆旦诗集·附录.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120.],并指出其诗艺的特点在“肉体与形而上的玄思混合”;在1980年代以来的批评和解读中,更进一步被确认为新诗中最著名的经典作品之一,孙玉石先生誉之为“中国现代的《秋兴八首》”[孙玉石. 解读穆旦的《诗八首》[M].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2.]。郑敏、孙玉石、梁秉钧、王圣思、张同道等诗人和批评家从不同角度对这首诗的意义进行了多层次的挖掘,为我们深入这首诗“幽暗”的内部提供了必要的光源。郑敏先生认为这首诗表现的是“个人爱情经历与宇宙运转的联系”,它包含着“双层,三条力的结构”。所谓“双层”就是始终贯穿在八首诗中的“既相矛盾又并存的生和死的力,幸福的允诺和接踵而至的幻灭的力”,“三条力”则是指诗中“我”“你”“上帝”三种力量的矛盾与亲和。这种多重力量的“交织,穿梭,呼应,冲击”既构成诗歌发展的基本动力,同时释放出能量,感染读者,并引致读者和诗之间的对话。[郑敏. 诗人与矛盾[M].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38~39.]郑敏先生的这一阐释,我以为是迄今为止对这首诗的深层意义最为内行和到位的把握,是我们进入这首诗的内部可以依赖的最明亮的一束光线。但是,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光源汇集到一起,也并不能完全照亮这首诗内部的天空,它的一些部分仍然被重重阴影遮蔽着,而对其中一些细节的解释也远没有达到圆融透彻的地步。这也许再一次证明了,一首好诗的意义是永远无法穷尽的。本文试图借助这些前人的指引,以自己暗昧的心智在照耀这首诗的光源中增加一支微明的、朦胧的火炬——如果它碰巧照亮了某些被前人忽略的角落,则笔者就感到非常满意了。
下面我们按八首的顺序逐首进行解读。
一
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
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
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
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第一首诗奠定了整个组诗情感的基调,也确立了它以玄思作为诗情发展动力的基本方法论特征。郑敏先生所谓的“双层,三条力的结构”在这第一首诗里得到了初步展示。在这里,我们既看到了燃烧的热情,也看到了对这热情的否定;既看到了纵火犯,也看到了消防员——郑敏先生所谓的“双层结构”,在我看来,实际上体现了爱的肯定与否定、可能与不可能两个互相纠缠的方面,它们分别构成了组诗的第一主题和第二主题。整个组诗就是通过这两个主题之间的对话和驳难来展开的,正是它们之间时而互相平行、时而相互交缠的运动构成了这首诗的基本结构线索。而郑敏先生所谓的“三条力”——“我”、“你”、“上帝”(也都在这里登台亮相了)——作为推动上述主题发展的内在动力,本身都包含了爱的可能与不可能(肯定与否定)的双重因子,彼此之间又不断地互相交缠、辩驳、冲突、对话,从而推动诗歌主题不断向前发展。实际上,这第一首诗就像整个组诗的全息缩微,包含了其后各首诗的中心内容,实际上,下面七首诗在相当程度上都可以看作这第一首诗的比例不等的“放样”。更确切的说,它就像一粒花种;在其后各诗中,这粒种子逐渐萌蘖、发芽、抽枝,直到开放为完全的花朵。
在传统的情诗里,一般出场的只有“我”和“你”两个角色;只有在极少的、阴郁的情诗里,才会出现第三个角色“他”。这个“他”,有两个最基本的形象范型——情敌或者死神。在这样的诗里,“他”既是使“我”和“你”分离的否定的力量,同时也是使“你”和“他”结合的肯定的力量——“死神”实际上只是一个特殊的情人。穆旦这首诗中的“上帝”,却是一个更为危险的对手,他一方面暗中为有情人撮合,另一方面却悄悄败坏情人之间的感情;他不是情敌,却比情敌更难以对付。下面我们会看到,他经常深入到我们内部,从内部推翻我们的承诺,从而造成我们彼此的背离。这首诗正是从否定开始来发掘爱情的秘密的。在罗曼蒂克的想象中,爱情永远是一个积极的、肯定的、幸福的、理解的力量,但是经验和观察却告诉我们,爱情也是一个否定的、灾难性的力量,幸福与灾难就像爱情不可分割的两面。诗的第一句,“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就把爱情这否定性的一面和盘托出。“火灾”是我心中燃烧的、不可遏止的热情,但它不也是毁灭一切的灾难的起点吗?对海伦的爱情烧毁了特洛伊,对褒姒和杨贵妃的爱情几乎烧毁了伟大的周王朝和唐王朝——这并不是文学性的比喻,而是我们每个人血液中的经验,我们都在这样的火焰中经受过无情的炙烤。这一句同时也暗示了这组诗的性质:我们将要读到的不是什么浪漫爱情的幻想曲,而是试图揭示爱情真相的“经验之歌”。接下去第二行诗仍然是一个否定句,“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爱情在这里走向理解的反面。“我”的热情为“你”而燃烧,但正是这种燃烧的热情遮蔽了真正的“我”,阻碍“你”对“我”的真正了解。接下去是又一重否定:“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你底,我底”。这是把燃烧的热情和“你”“我”的关系也否定了。就是说,那燃烧的热情也并不真正属于“你”“我”,而仅仅属于下文所说的“自然底蜕变底程序”,只是一个预先规定的程序的一部分。按照现代生物学观点,所谓情爱的发生仅仅起于我们脑垂体分泌的化学成分的微小变化。这种生物学观点完全推翻了人们在情爱领域长期以来拥有的一种浪漫观念,揭示出爱情的内在的生物学基础。也就是说,在爱情中,我们并没有自由可言,一切不过是照自然的程序按部就班地运行。所以,我们相爱,而我们依然“相隔如重山”。近代罗曼蒂克的爱情观念,其雏形来自西方的骑士传统,而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明传统中得到培育,并最终在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平等”(不只是男女平等)观念的催化下定形。在这一传统中,爱情一直被视为一种高贵的私人感情,因其最完全地体现了人类的自由意志,而被赋予了崇高的人性价值。在近代浪漫文学中,这一观念得到了无以复加的张扬。但是这种乌托邦式的爱情理想很难见容于现实,经常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所以,浪漫文学的题材常常是悲剧性的,其典型的情感体验则是忧郁的、悲伤的、愤世嫉俗的。穆旦这组诗正是对这种罗曼蒂克的情爱观念的一个修正,其依据则是现代科学的客观性。当然,这种修正并不是要全盘否定这一情爱观念,而是要赋予这一情爱观念新的内容,以使这一观念获得理性的支持,立足于更加牢固坚实的基础,从而获得克服现实的新的力量源泉。我以为,这可以视为这组诗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动机。
“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我”意识到“我”的爱情只是自然的蜕变程序的一部分,但仍然要爱,而且义无返顾,爱情在这里就具有了某种悲剧的意味。后一行中的“暂时”在这首诗里具有丰富的意韵——“暂”与“永”的关系正是这组诗试图解开的关于爱情的也是关于人生的谜团之一——这一意韵将在以下各诗中得到进一步的显示,我们在这里先按下不表。“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郑敏将这一句理解为“暴君上帝玩弄着情人们让‘我’多次生死”[郑敏. 诗人与矛盾[M].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34. ]。这是把“变灰”的“灰”理解为“归于尘土”的“尘土”,似乎不确。穆旦自己对这一行的英译是这样的:“Though I weep, burn out, burn out, and live again”。[穆旦. Poems(《诗八首》英译)[M]. //穆旦诗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81.]可见这个“灰”是“燃为灰烬”的意思,是指恋爱中灰心、绝望的体验。当然,如果从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郑敏的话,也说得过去,因为爱情中绝望的经验,也正与“死亡”类似。郑敏以“暴君”称呼诗中的上帝,我以为不妥当。穆旦并不是一个教徒,他也不是从宗教的意义上来使用“上帝”一词的。在他的诗中,“上帝”更多地是“自然”的人格化。它体现了一种不可抗拒的、“不仁”的“自然底蜕变底程序”,但它本身对我们并不抱有任何的敌意。因此,它并不是“暴君”。最后一句“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是说“我”本来是上帝的造物,他又让我不断地经历绝望和新生,那无异于他玩弄自己。
二
水流山石间沉淀下你我,
而我们成长,在死底子宫里。
在无数的可能里一个变形的生命
永远不能完成他自己。
我和你谈话,相信你,爱你,
这时候就听见我底主暗笑,
不断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
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
第二首诗意是对第一首中“自然底蜕变底程序”和“暂时的你”两个意象的展开。“水流山石间”是一个关于自然的形象,“水流山石间沉淀下你我”是说“你”“我”都是自然的蜕变程序的产物。“而我们成长,在死底子宫里”,这一行诗中包含着一个深刻的“生”与“死”的矛盾。“死底子宫”是典型的矛盾修辞。“子宫”是孕育生命的所在,诗人却用“死”来限制和修饰它。郑敏对这两句的解释是,“‘水流’是活力,但成胎后却被监禁在‘死底子宫里’”[郑敏. 诗人与矛盾[M].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35.],孙玉石先生则认为“死底子宫”“象征一件事物(包括爱)于一定的时间(相对静止的时间)中的孕育诞生”[孙玉石. 解读穆旦的《诗八首》[M].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2.]。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解释都不过按照字面意思“曲为之解”,并没有揭示出诗歌的真正内涵。我以为在“死底子宫”这一矛盾的修辞里,包含了诗人对生命的一个极为深刻的认识。子宫本身既是孕育生命的所在,同时它也是孕育“死”的所在——“死”正是在子宫里与“生”一同被孕育的。里尔克在《马尔特手记》中写道:“那该是怎样一种忧伤的美啊!当女人怀了孕,站在那里,纤柔的双手下意识地放在她们那大起来的腹部,那里面怀着两个果实:一个小孩和一个死。在她们那极其茫然的脸上所绽露的宽宏,甚至可说是富于营养的微笑,难道不正是由于她们有时会想到这两种果实都正在她们的肚腹里生长吗?”[里尔克. 马尔特手记[J]. 曹元勇译. // 上海:收获(长篇专号),2006秋冬卷:237.]穆旦在这里进一步把这个生与死的同一性推向极端,他不说子宫同时孕育了“生”和“死”,而说“死”正是使我们成长的子宫(注意,这里用的是表示所有关系的“底”,而不是表示修饰关系的“的”):“死”不但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它也是我们的成长最后的终极,因此也正是它孕育着、催促着我们的成长。这个思想某种程度上比里尔克的思想更深刻地揭示了“死”在人生中的确切位置。“在无数的可能里一个变形的生命,/永远不能完成他自己”,这是说我们永远处在“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永远不可能获得最终的定型。汉语中“盖棺定论”的成语包含了对这一命题的朴素认识,也就是说,在死亡最终结束我们的变形之前,我们永远都处在一种“未完成”状态。说到底,我们的生命就是不断地变形,不断地占有,又不断地放弃。无数的机缘、偶然、时刻、人物、事件、情感、思想、风景、谈话,在我们的一生中不断进入我们,占领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处于永不停息的变化之中,并最终沉淀、凝定为我们身上的一部分。这个思想惠特曼在《有个天天向前走的孩子》一诗中以其特有的乐观主义的、天真的态度做过生动的表达。穆旦在这里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但却出之于一种成熟的、经验的态度。这样,所谓爱情的盟誓,就是在两个不断变化的、不确定的主体之间交换誓约,这样的誓约可能是永恒的吗?
第二节诗是对上述疑问的回答。恋人满怀信心地宣扬他的爱情,把他的爱情视为生命的最终实现和完成,轻易地相信它许诺的永远。然而,就在恋人宣布他的爱情的时候,上帝已经悄悄地添来新的“你”“我”,让“你”“我”不知不觉离开了原来的位置。欧谚云,“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也可以说,“人类一恋爱,上帝就发笑”。不断的改变使我们丰富,但也使我们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而这危险对恋人的信心是致命的。
香港诗人梁秉钧曾经引这首诗来分析穆旦诗中的“自我”。他认为从这首诗和穆旦其他一些诗中反映出穆旦的“自我”是不完整、不稳定的,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体现了194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自我”的一种比较复杂而深刻的认识。[梁秉钧. 穆旦与现代的我[M].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43~54.]这是极有见地的。而这种“自我”是变化的认识,也使诗人对爱情产生新的认知和体验。这组诗正是这种新的认知和体验的产物。
三
你底年龄里的小小野兽,
它和春草一样地呼吸,
它带来你底颜色,芳香,丰满,
它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
我越过你大理石的理智殿堂,
而为它埋藏的生命珍惜;
你我底手底接触是一片草场,
那里有它底固执,我底惊喜。
这一首可以看作是从第一首中“成熟的年代”这一意象中生长、发育出来的。在这一首诗中,“上帝”暂时退场,“你”“我”似乎暂时获得了某种自主性来演绎你我之间的“爱”的戏剧(当然,这种自主性是并不可靠的,因为“你”“我”无论如何仍处于“自然底蜕变底程序”的掌握中)。这里第一行中的“你底年龄”也就是第一首所说的“成熟的年代”。从这成熟的年龄里孕育出了一只“小小的野兽”,它赋予“你”一切青春的魅力:让“你”的呼吸充满青草的芳香,让“你”的脸颊一天天红润,也让“你”的乳房骄傲地耸起。而这一切只是为即将来临的“爱”精心准备的诱惑:“它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温暖的黑暗” 可以说是对“爱”的最恰切的称呼,而“疯狂”则是诗人对“爱”的性质的界定。“爱”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力量,它来自全部生物的进化史,从它那里我们可以倾听到无数生物学、遗传学的祖先向我们发出的悠远的呼唤。里尔克把这一在我们血液中主宰着我们情欲的力量称为“隐藏着罪恶的血腥的海神”,他以“恐怖的三叉戟”武装自己,在我们心中煽起“暗黑的风”。所以,少女不经意的柔情在情人的心中唤起的是整整一个洪荒时代,“在我们之间相爱,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未来的存在,/而是无数的逝者;不是单一的孩儿,/而是犹如山岳崩陷,在我们的底层/躺卧的父亲们;而是过世的母亲们的/干枯的河床——”。[里尔克. 杜伊诺哀歌·第三哀歌[M].李魁贤,译//臧棣.里尔克诗选.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285~288.]里尔克对“爱”的这种认识受到了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在穆旦对“爱”的冷峻认知中,我们同样可以辨认出这种影响的痕迹。里尔克出于他的女性膜拜,似乎认为这种主宰我们情欲的黑暗力量主要在男性身上发挥其影响,而穆旦显然认为在女性身上隐藏着同样的力量。在成熟的年龄来临的时刻,“你”血液中的小小的野兽,也成了“你”行动的主宰,“它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爱”既是一种使我们结束孤独之寒冷的伟大的统一的力量,又是一种令我们陷入危险的疯狂的、毁灭的力量——在我们古老的血液中,恐怖的怪物冲我们眨着眼,微笑着,要把我们的灵魂彻底掠走……这就是“温暖的黑暗”向我们昭示的意义。
上一节讲“你”在“自然底蜕变底程序”引导下为爱所做的精心准备,第二节则说“我”对“你”的征服。这个征服首先是克服“你”的“理智”。“理智”提醒我们“爱”的危险,它是唯一在“爱”的征服与被征服中保护我们的力量,而“我”要想占有你生命中的珍宝,首先必须越过“你”的“理智”的防线。因此,“爱”的第一战就是让“理智”缴械。经过一番鏖战,“我” 终于摧毁了“你”的“理智”的全部防御力量,占有了“你”“埋藏的珍宝”,“我”为此格外感到一种“爱”的珍惜。“而为它埋藏的生命珍惜”一句不太符合语法规范,按照正常的语序似乎应该写为“而珍惜它埋藏的生命”或者“而为它埋藏的生命感到珍惜”。这个“它”是指上一行出现的“理智的殿堂”。我的这个理解可以从穆旦自己对这两行诗的英译中得到验证。他对这两行的英译是“I’ll dig through your granite temple of Reason/ And there, his long buried years will rescue”,意思是我挖穿了你大理石的理智殿堂,从中拯救了你的被埋藏在那里的生命。一旦“理智”的抵抗被摧毁,“你”“我”心灵中那被束缚的本能的力量也就得到了解放,从而让我们完全沉浸在爱情的感官的狂喜里:“你我底手底接触是一片草场,/那里有它底固执,我底惊喜。”“草场”是一个明媚的阳春景象,这里代表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蓬勃的感官的生命力。草是穆旦用来象征生命力量惯用的意象,在他写于同一时期的另一名篇《春》中,有这样的诗句:“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此处“草”的用法和本诗的“草场”类似,只是“草场”所传达的生命力量更蓬勃,更飞扬生动,更无遮拦。“它的固执”的这个“它”既可以指上一节的“年龄里的小小野兽”,也可以指上一行中代表“理智”。在沉睡的感官力量被唤醒之前,“固执”是一种矜持,在感官的力量被唤醒之后,“固执”又是一种执著和坚持,“惊喜”则代表了“我”的胜利的喜悦。这几行诗里有着诗人关于情爱的最深切的个人体验。
四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
那窒息着我们的
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
它底幽灵笼罩,使我们游离,
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
这一首承上一首而来。上一首开始写到两个人的“手底接触”,这一首进一步写属于两个人的令人沉迷的“爱”的小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首里,人称代词一律用的是“我们”。这在全诗各首中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的情况,由此也可以推断这一首在全诗结构中处于一个特殊地位。这里的“我们”可以说代表了“你”“我”的情爱发展到了一个合一的境界。这是一个“爱”的小高潮,但那威胁着“爱”的封闭世界的各种力量并没有消失,“未成形的黑暗”仍然在暗中窥伺着,在表面的平静和幸福中一直潜藏着危险的旋涡。而这种矛盾力量的存在正是整个组诗发展的基本动力。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这里的“言语”,不应当仅仅理解为爱的言语表达,而应该理解为传递爱的信息的各种方法、手段,包括恋人之间心灵和感官的一切交流。爱是世界之光,而以恋人的身体和心灵为燃烧的烛芯——它照亮了、划定了两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它之外的广大的世界在性质上和形态上几乎完全对立,在这里,奉献、给予、施舍是快乐和满足的源泉;恋人们甘心地互为对方的牺牲。而在这个有限的世界之外,实行的则是另一套人所共知的完全不同的世俗规则。“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是说爱的幻觉般的光亮只能照亮两个人的有限的小世界,在它之外,则是黑暗(这是所有那些世俗规则的共同性质)的统治,是与爱的世界相对峙的现实的阴郁世界;这个世界无时无刻不想吞没爱的世界那点动摇的、微弱的、颤抖的光芒。但是沉浸在爱的幸福中的恋人并不理会这个世界的阴险企图,他们天真地把他们自己的世界当作整个世界,把这个“爱”的小世界的性质推定为整个世界的性质,那可怕的吞没一切的“黑暗”对他们暂时并不存在(因而它似乎是“未成形的”),他们只一味沉迷于那“可能的和不可能的”爱的快乐和满足中。为什么“爱的不可能”也会像“爱的可能”一样使我们沉迷?这里涉及一个心理学上的秘密——越是我们得不到的东西,对我们越具有魅力。也就是说,爱的魔力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它的不可能。那使情人们沉迷于其中的,并不是——至少不全是——“爱的可能”,而是——或者很大程度上是——“爱的不可能”。这个秘密在恋爱心理学上是一个发现。对这一思想,诗人在下文还有进一步的发挥,这里我们先暂时放下。上一行“未成形的黑暗”,孙玉石先生认为与上一节“温暖的黑暗”的“黑暗”是一个意思,是“情感历程中的一种境界”,“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爱得昏天黑地’的意思”,也可备一解。[孙玉石. 解读穆旦的《诗八首》[M].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4.]但是这样理解难免把诗中被爱的光亮所“照明的世界”和“黑暗”之间的对峙感消解了或者说削弱了,把爱的两难之境简化为单纯的沉迷。我以为这可能是对诗意的一种削减。
“那窒息着我们的/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这一句仍然是说爱的感官的和心灵的迷狂。“窒息”是指由爱的迷狂所带来的极度的紧张。“言语”还是指恋人之间“爱”的信心的交流。后一句中的“未生即死的言语”,一方面昭示了“爱”的语言的速度——爱的语言不断被发明、被说出,以至旧的还没有被说出,新的就已经产生,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爱”的即时性。爱的渴望随时产生,并要求即刻的满足,而满足会产生厌倦,不满足又会腐蚀爱——无论满足还是不满足都会使爱变质,催促它走向自己的反面。也就是说,“爱”即使在“爱”的行动中,其边界也是不断移动和变化的,并没有凝固的、像雕塑家在大理石上定型的那种永恒的“爱”——它也正是前一行所谓“窒息”感的来源。“它底幽灵笼罩,使我们游离,/游进混乱的自由和美丽”中,这个“它”是指什么呢?孙玉石先生以为是指第二首中的“我底主”,在这里代表了理智的力量,“它”要使我们彼此“游离”。[孙玉石. 解读穆旦的《诗八首》[M].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5.]我认为这样解释可能有些牵强,第二节中“我底主”的人称代词是“他”,如果这里还是指“我底主”,没有道理忽然又改用“它”。“使我们游离”解释为使“你”“我”彼此游离,也似不妥。我认为这里实际上隐含了一个被省略的补语成分,完整的表达应该是“使我们游离于世界”,也就是沉迷于“爱”的小世界的意思,和前一节的意思一脉相承。这样,这个“它”就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承上一首的“它”,指“你底年龄里的小小野兽”,也就是感官的力量,二是直接承本节的“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指“爱”的交流。从语法上讲,后一种解释更合理,因为这几行之间用的都是逗号,意思是一气连贯的,“它”的来处不应该隔那么远。按这样理解的话,这两行的意思就是,“你”“我”笼罩在爱的愿望和要求中,因而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游进了混乱的(也就是丰富的、匆促的)爱底自由和美丽中。
从结构上说,这第四首诗是整个组诗承上启下的枢纽。正如我们前文已经指出的,这一首的第三行“那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一句概括了全诗的核心主题。以上各诗中,第一首是爱的可能和不可能两大主题的初步显露,第二首主要是对第二主题“爱的不可能”的发展和变奏,第三首主要发展了“爱的可能”的主题,第四首对前三首进行小结,两个主题在经过中间两首的独立发展之后在这里再次相遇。它们在这一首里汇合和稍做停留之后,又继续各自独立地向前发展,直到在最后一首中演变成“合一”的协奏。
五
夕阳西下,一阵微风吹拂着田野,
是多么久的原因在这里积累。
那移动了景物的移动我底心
从最古老的开端流向你,安睡。
那形成了树林和屹立的岩石的,
将使我此时的渴望永存,
一切在它底过程中流露的美
教我爱你的方法,教我变更。
在这一首中,诗人以一个幸福的恋人的身份赞美和咏叹“爱”的永久和丰富,可以说是对“爱的可能”的主题的华采的发展。它利用了第一首中“自然底蜕变底程序”作为变奏的基础,而进行了反方向的发展——在第一首中,“我”在这个自然的秩序里看见的是生命的短暂,在恋人的身上看到的是一个“暂时的你”,而在这一首中,“我”却看到了“爱”在自然秩序中的“永存”。这一首也是整个组诗中抒情性质最强烈的乐段(“你”和“上帝”在此暂时退场,同时也使这一首成为整个组诗最具独白性质的部分)——当然,沉思仍然是诗歌的基调。
在这一首里,“我”作为一个从“幸福”的窗口向外张望的恋人,在一切事物中都看到了“爱”的力量、爱的秩序,并试图从自然的秩序里学习丰富和完善“爱”的方法。从夕阳西下,微风吹拂田野的平常而美好的景象中,“我”看到了“爱”的悠久的原因。在“我”看来,眼前的一切景物决不是偶然的凑泊,而都有着它的悠久的、必然的根源,它们无不体现着宇宙本身的意志:“是多么久的原因在这里积累”。而正是同样的原因催促我“从古老的开端流向你,安睡”。“安睡”也就是上一首诗所说的“静静拥抱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是心灵在“爱”的世界里的安憩。“那移动了景物的”“那形成了树林和岩石的”都是指时间,也就是第一首中所说的“自然底蜕变底程序”、“上帝”,它体现了自然本身的进化意志。正是它使世界成为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这个原因同样也“将使我此时的渴望永存”,因为它使“我”的“爱”有了来处和去处,而不再是暂刻的,即生即灭的。自然在它的变化和进化中表现出形态万千、不断更新的美,也教会我“爱你的方法,教我变更”。——“爱”也同样需要不断的丰富和增益,“爱”的停滞和凝固,也就意味着“爱” 的死亡。这一首一反第二首的悲观态度,从变化中引出了积极的意义。
六
相同和相同溶为怠倦,
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
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窄路里,
我制造自己在那上面旅行。
他存在,听从我底指使,
他保护,而把我留在孤独里,
他底痛苦是不断的寻求
你底秩序,求得了又必须背离。
这一首可以说是上一首的反命题,在上一首把“爱的可能”推上高峰之后,这一首则把“爱的不可能”的主题发展到了自身的巅峰。前一节指出,“爱”是一条危险的窄路。“相同和相同溶为怠倦,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是说 “同”造成怠倦,“异”又使我们彼此陌生——因而潜藏着种种不可知的危险——“同”和“异”都会妨碍“你”“我”真正相爱。这种两难之境酿成了无数的“爱”的悲剧。所谓,“不了解使我们相爱,了解使我们分离”就是这“爱”的两难之境的体现。
第二节比较费解。关键的问题是,这里的“他”指谁?孙玉石先生认为这一节里的几个“他”“均指造物主,也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自然界和一切生物的创造者”[孙玉石. 解读穆旦的《诗八首》[M].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8.],郑敏先生则认为这里的“他”是“我”的分裂,“他”指外在的“我”,而“我”则是“将自己封锁在寂寞孤独里的那个人格”[郑敏. 诗人与矛盾[M].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37.]。我以为郑敏先生的解释更为合理。按照孙玉石先生的理解,这一节诗几乎是不可解的,勉强为之解释,也难于自圆其说。而郑敏所说的“自我”分裂正好印证了梁秉钧在穆旦的诗里所发现的“自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我个人认为,“他”在这里是指行动并敏于感受的“自我”,而“我”则是观察着这个行动的“自我”的另一个沉思的、处于意识控制之下的“自我”。这两个“自我”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和“自我”,它们既有互相依赖,互相支持的一面,同时又处于矛盾和冲突中。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本我”依照享乐原则行事,不惜一切代价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自我”则依照现实原则行事,努力节制“本我”不合理的行为。但穆旦这里的“他”和“我”并不完全等同于弗洛伊德的“本我”和“自我”,而更多地表现为“自我”的两种不同状态,因此,他们之间的冲突不像“本我”和“自我”那么强烈,彼此之间的依赖则更明显。“他存在,听从我底指使”,可以理解为意识对行动的控制、节制,“他保护,而把我留在孤独里”则反过来强调行动对意识的支持——如果行动的“他”出于保护的本能而在追求“爱”的行动中裹足不前,那就是把“我”留在孤独里。最后两行是说,“他”在“爱”的窄路上不断地寻求向“你”靠近,渴望融入“你”的秩序,但是一旦求得,彼此之间的适应、同化又使“相同和相同溶为怠倦”,“他”几乎又本能地寻求背离。“爱”的本意,可以说就是在“异”中寻求自身的完善和丰富。所以,“同”较之“异”更是“爱”的大敌。由此可见,“爱”本身包含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我”一方面渴望通过与陌生的“你”结合,从而扩展、丰富和完善自己,另一方面结合所伴随的适应和同化又成为背离的起点,使“爱”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这也就是“爱”的最大的不可能。
七
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
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
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
让我在你底怀里得到安憩——
呵,在你底不能自主的心上,
你底随有随无的美丽的形象,
那里,我看见你孤独的爱情
笔立着,和我底平行着生长!
这一首又回到“爱的可能”的主题。在“不可能”的主题发展到顶峰之后,“可能”的主题要求有一个同样的发展,以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同时,在“可能”的土壤里,“不可能”的种子仍在悄悄地萌蘖。
第一节揭示了“爱”的根本动力——“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说“爱”的根本动力是恐惧,似乎有些危言耸听,却正在情理之中。我们最大的恐惧是死亡,而爱欲正是产生于对死亡恐惧的克服。爱欲的最重大的后果是通过基因复制达到个体的延续和种族的繁衍。而对人类来说,爱欲的另一个可能具有同等意义的后果则是“爱者”互相分担对死亡的恐惧,从而克服我们心灵上的孤独——对孤独的恐惧同样来自死亡的阴影。“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这些具体的形象都指向对孤独的恐惧;“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这些抽象的名词在诗中也各有所指。“丢失”意味着欠缺和不完整,意味着寻求,意味着对完全的渴望。它自然会让我们想起,柏拉图在《会饮篇》里借阿里斯托芬之口叙述的那个关于爱情起源的神话故事。这个故事说,世界上本来存在男人、女人和阴z 阳x 人c三种人,他们的身体都是圆的,各有四手四脚和有两副面孔的一个圆形的头。这种人都有无穷的力量,因此想图谋反抗众神。宙斯为了惩罚他们,把他们劈成了两半。阿里斯托芬说,“所以我们每人只是人的一半,一种合起来才见全体的符”,为了恢复原始的整一状态,“每个人都常在希求自己的另一半”。这样,被劈开的男人就成了男同性恋者,被劈开的女人成了就女同性恋者,被劈开的阴z 阳x 人c则成了异性恋者。[柏拉图. 会饮篇[M]// 文艺对话集. 朱光潜,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238~241.]因此,企求与“丢失”的另一半重新汇合就成了“爱”的原始的动力。“记忆”则把“爱”的起源推向悠远的过去以至史前的生物进化史。在这个意义上,“爱”正是宇宙意志的体现。而全部关于“爱”的漫长进化史都凝聚在我们的潜意识——那最深远、最悠久的记忆中。“爱”绝不是一个纯个体的、独立的行为,正如里尔克在他的《杜伊诺哀歌》第三首中所吟唱的,我们相爱,绝不是“我”和“你”之间的一个单一的“未来的存在”,而是一个可以上溯到古老历史的复杂的事件,它在“我们”身上延续着无数的男性祖先和女性祖先之间的一场永恒的争斗。“永续的时间”则是死亡恐惧的另一个化身,所谓“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就是对于永续的时间和无尽的空间所产生的恐惧,而从根本上说,它同样来自对死亡的恐惧。所有这一切恐惧都要求在“你”的怀里得到最终的克服,“让我在你的怀里得到安憩”。“爱”的伟大意义不就在此吗?
第二节诗有些费解,主要是“你底随有随无的美丽的形象”一句的语法关系不很明确,因而造成理解上的困难。穆旦本人对这一节头两行的英译文为“Ah, in your heart that’s never self-controlled/ and your beauty that comes and goes”,则“你底随有随无的美丽的形象”和“你底不能自主的心”是并列关系,共同作为修饰“我看见”的状语成分,其实意思还是明确的:我在你不能自主的心上,也在你在我心上的随有随无的美丽的形象中,看见了你孤独地生长着的爱情。
第二节末两行诗里出现的这个“你孤独的爱情”,值得我们再三玩味。这一意象如同组诗中的其它众多意象一样,包含了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这意味着“我”的爱情终于唤醒了“你”的爱情,并使“你”的心“不能自主”。至此,“你”“我”的爱情完成了彼此试探、逗引、揣摩、侦察与反侦察、进攻与阻截、包围和反包围的全过程,而结成了统一的联盟。两个爱情携起手来,一起面对充满敌意的世界,尤其是“爱”的窄路上满布的一切危险。另一方面,“孤独的爱情”又表明,即使在“爱”中,我们仍然是孤独的,并不能心心相印,达到彼此的完全融合,因而充满了“我爱你与你无关”的无奈。“爱”要求我们放弃自我,放弃自主,完全地献出我们自己,而自我又是“爱”的主体,放弃自我、无主体的“爱”因而又是没有价值的。这既是“爱”的困境,也是“自我”的困境。这一意象在穆旦本人的英译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强调。穆旦对这两行的英译是这样的:“Where, parallel to my passion of love, I find,/ Yours is growing so lonely”。在英译中,穆旦实际上把“孤独”放到了全句意义的中心,使上述在中文中还比较隐晦的内涵得到更为醒豁的表现。
这一节诗的最后两句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当代诗人舒婷《致橡树》中为人传诵的名句,“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但这两行诗的含义却要比舒婷那全首诗的含义更为丰富、深刻,洞悉更多关于“爱”的秘密。舒婷在那首诗里提出了“爱”的独立性的问题,但对“爱”本身并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也就是说,诗人对“爱”本身仍然抱着单纯的信仰。而在穆旦这两行诗里,不仅包含着对“爱”的独立性的思考,而且包含了对“爱”的困难的深刻意识,它从“爱”的内部出发走向了“爱”的不可能。对穆旦来说,“爱”的可能必须建立在对“爱”的不可能的克服之上。“平行”一方面意味着“爱”的独立,“爱”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占领、兼并、统一、吞灭,而是双方在保持独立基础上的联合、结盟、呼应、支持和声援,然而,另一方面,诗人也意识到,与“爱”的独立性毗邻而住的却是“爱”的“孤立性”。“爱”是从一个人的内心生长起来的,它是在孤独中孕育的苍白花朵——“爱”就是所谓谙尽孤独的滋味——这可能是诗人用用“孤独”来修饰“你的爱情”的另一个原因。正是我们心上那些“随有随无的美丽的形象”,那些幻想的、飘忽的、不知所来也不知所终的,滋养了它。“我”的和“你”的“爱”,各自在我们的内心独立地酝酿、发育、生长——“你”“我”对它既不能自主,更不可能互相做主——它们之间并不天然地互相理解,相反,它们天然地互相陌生,彼此猜忌,甚至互相敌对。这是“爱”的不可能的另一重含义。——然而,也正是这种“爱”的孤立性使爱的双方保持了必要的距离,为“爱”的生长留出了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爱”的可能要依赖于它的不可能。可以说,第二首从“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发现了“爱”的否定,第六首从一个人的“爱”本身发现了它的否定,本首则从“爱”涉及的“我—你”关系中发现了它的肯定和否定的互相交缠、辩驳、统一。积极的力量包含在本首的最后一个词语——“生长”——中。“生长”意味着变化和更新,它使“爱”发生变迁,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但它也包含了理解的意愿、可能性和能力。与变化所蕴含的危险相比,停滞是“爱”的更大的敌人,它意味着理解的意愿、可能性和能力的死亡,也就是“爱”本身的死亡。所以,“爱”本身呼唤着随时更新,不断生长——那是使“爱”始终保持活力的唯一有效的强生处方。
八
再没有更近的接近,
所有的偶然在我们间定型;
只有阳光透过缤纷的枝叶
分在两片情愿的心上,相同。
等季候一到就要各自飘落,
而赐生我们的巨树永青,
它对我们的不仁的嘲弄
(和哭泣)在合一的老根里化为平静。
全诗最后一首,在“爱”的可能与不可能的双重主题的协奏中结束全篇。“我”“你”“上帝”三个决定诗歌发展的基本的“力”在历经种种矛盾、斗争、亲和之后在这里重新聚首,并达到了某种程度的交融与和解。对这一首的含义,过去的批评存在多种不同的理解。张同道认为,本首以“高度的圆融——爱情的完满结束”,“所有的对抗、纠缠、反讽,‘在合一的老根里化为平静’,二对元素在此和解”,并据此认为,“后二首与前六首之间失去了一个转化的环节,损害了此诗的圆美”。[张同道. 带电的肉体与搏斗的灵魂:穆旦[M].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81.]孙玉石先生认为,“诗人在这里奏出了人类生命的真正的爱情,也是诗人‘你我’自己的‘我们的爱’的‘巨树永青’的赞歌”,“这是诗人用他整个的生命体验和认识唱出来的一段对于人类的爱情,也是自我的爱情的永恒的赞歌”。[孙玉石. 解读穆旦的《诗八首》[M].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0~31.]郑敏先生则认为,这一首诗中包含着诗人对爱情的“最后的绝望”,充满了“庄严肃穆的冷寂凄凉情调”,“显得有些放弃挣扎和斗争”。[郑敏. 诗人与矛盾[M].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38.]这些阐释有的截然相反,有的同中有异,但对诗意的理解都还没有达到圆融妥帖的地步。张同道和孙玉石先生的理解偏重于第一节诗所表现的“爱”的完成,并把最后一行的“合一”与“平静”理解为矛盾的最终解决。郑敏则把“不仁的嘲弄”视为爱情的敌对力量,而把这一首理解为“爱”对这一敌对力量的最后的诅咒。他们或者寄望在这最后一首里各种矛盾达到最终的和解,或者希望爱的最后战胜。但是,要取得这两种结果事实上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各种矛盾要达到最终和解,只有通过中国式的、多少有些自欺欺人的委任造化,这显然不是诗人所希望的结果。而爱的最后战胜也是一种幻想。那么,还有什么积极的、有意义的后果是可能达到的呢?这一首的诗意强调在充分理解“爱”的可能与不可能的种种矛盾、冲突、亲和因素的基础上,获得一种关于“爱”的明澈的意识,并以这一意识为指导,自觉地调整“爱”的行动,把本能的、盲目的“爱”转化为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为。这样,也就让“爱”的诸种矛盾、冲突、斗争的因素在意识的参与下得到某种程度的和解,从而把“爱”的不可能转化为某种积极的力量。我以为这最后一首的意义乃在于此。
这里的第一节诗写出了“爱”的可能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几乎可以说是圆满的境界,“再没有更近的接近”,两颗情愿的心像两片紧邻的树叶,同等地分享着“爱”的阳光,所有的偶然在这里凝结为“爱”的必然。这几乎已经接近了“爱”的完成。所以,在这一首里(和在第四首里一样),不再有“我”和“你”的分别,它们联合为一个“爱”的共同体——“我们”。然而,进入到第二节,那个与“爱”的肯定力量如影随形的“爱”的否定力量又出场了,而且这一次是最彻底的否定——死亡——它一举就摧毁了“爱”的全部成果。“各自飘落”可以说是对“爱”的孤立性的最彻底的揭示。那永青的巨树既不会因为我们的“爱”而赐给我们“永青”的光荣,也不会赐给我们另一个次一等的光荣——一个共同的死。死把人生最后的真相揭示给我们,说到底我们都是孤独的、单个的个体: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独自去面对自己的死,任何人——即使有人爱我们胜过自己的生命——也无法为我们分担这一人生的后果。这就是那永青的巨树所代表的“自然底蜕变底程序”,对我们也是对我们的爱的“不仁的嘲弄”。然而,括弧里的哭泣指什么呢?我曾经认为,穆旦这个括弧的用法和卞之琳《距离的组织》那个著名的括弧相似,用来提醒读者“嘲弄”和“哭泣”分属不同的主体。也就是说,这个“哭泣”不属于永青的巨树,而属于“我们”。最后两句的意思是,巨树对我们的嘲弄和我们无助的哭泣在合一的老根里化为平静。孙玉石先生则认为,这个“哭泣”既可以指第一节诗中的“我哭泣,变灰”的哭泣,也可以指“上帝”为“他”的痛苦而哭泣,并认为后一种理解更顺畅。[孙玉石. 解读穆旦的《诗八首》[M].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1.]参见穆旦的英译,这两句为“While the huge tree that gave us birth will ever be green,/ but what to us his malicious mocking/ and his weeping……”则明确将“哭泣”归于“永青的巨树”。看来,孙玉石先生认为更顺畅的理解更符合诗人原意。回头再想,这一节头一行已说到“我们”的“各自飘落”,则“我们”的“哭泣”根本已无从说起,我的理解从开头就是错的——我实际上是被“嘲弄”和“哭泣”表面的矛盾所迷惑了。那么,怎么解释这个矛盾呢?我想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不仁”的嘲弄是就“我们”的角度而言,而“哭泣”是就“巨树”本身的角度而言。这里括弧的用处就在提醒我们这个区别。对“我们”来说,“巨树的”“永青”无异是对“我们”的“各自飘落”的“不仁的嘲弄”,而就“巨树”而言,它既赐生于“我们”,则对“我们”的“飘落”定然怀着深刻的同情,因而不由为之哭泣。那么,“巨树”对“我们”“各自飘落”的命运也是无能为力的。在这节诗里,“巨树”是作为“上帝”的对位语出现的,可见穆旦的“上帝”本身也受到“自然底蜕变底程序”的约束,而非宗教意义上绝对自由、绝对自主的上帝——郑敏先生把他称为“暴君上帝”是并不确切的。这个“上帝”更多的是“自然底蜕变底程序”的人格化。
在这一首诗里,爱的肯定与否定、可能与不可能是互相渗透的。因此,这个最后的“平静”并不是矛盾的最终解决,诗人其实也不指望有这样的解决。这样,我们也许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最后一行的“平静”。它或许是说,只要活着,“爱”就永远处于肯定与否定、可能与不可能、追求与逃避、分离与结合的矛盾、冲突与斗争中。所以,“爱”的真义并不是两个人的同化、同一,而是两个人在矛盾与冲突中不断地成长。
这一首是整个组诗诗情发展的高潮,而从诗艺来说,这一首也是全部八首诗中最为完美的。组诗具有鲜明的思辨与具体形象相结合的特点。但在前七首还难免存在思想溢出形象、思想大于形象的情况。但在这一首诗中,思想和形象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诗中的思想完全溶于形象中,像盐溶于水——我们尝到它的味道,却看不到它的形体。这里,诗人为决定全诗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自然底蜕变底程序”和“爱”的意志的冲突——找到了一个一体的形象:永青的巨树和它身上两片紧邻的树叶。这一形象自动地呈现了、揭示了上述对立面既互相冲突、一方又从属于另一方的根本性质,成为它的最贴切的、不可替代的载体。而上一节以“两片情愿的心”写“爱”的可能,下一节以落叶的飘零和树的永青写“爱”的不可能,在互相否定中最大程度地达到了构思的统一。所以,这第八首诗不仅是整个组诗诗情发展的顶峰,也是其诗艺发展的顶峰。可以说,整个组诗富有意味地结束于诗情与诗艺最高的结合点。
九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穆旦的这个组诗具有严格的有机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以“爱”的可能与不可能作为主题发展的主线,以“我”“你”“上帝”之间的矛盾、冲突、吸引、排斥、纠缠和对话为基本动力,通过它们之间的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的螺旋发展,揭示了“爱”的普遍真相。在这组诗里,诗人深入地探测、挖掘、解剖了“爱”的心理学、生理学、种族学以至宇宙学的根源,“使爱情从一种欲望转变为一种思想”(王佐良语)[王佐良. 穆旦:由来与归宿[M].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4.],在此基础上,最终建立了一种富于现代色彩的爱的哲学。对于“爱”的心理、生理和种族基础的探索,在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第三歌中就有深入的、突出的表现。事实上,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发表之后,这种探索就成为现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趋势。穆旦的这组诗也可以说是这一趋势的组成部分。如果放到新诗自身的历史来考察,这个作品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对题材和主题的现代性敏感,是1940年代以穆旦为首的一批青年诗人的共同追求,而寻求意识容量的扩张,多向度地开掘意识的层次,挖掘潜意识的深度,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意向。穆旦这组诗可以说是体现了1940年代中国新诗现代性追求所达到的思想和诗艺高度的一个代表性作品。就意识容量的丰富、主题开掘的深度而言,此前的新诗中显然难以找到与之匹敌的例子。这首诗的突出和成功之处,还在于它把一种相当抽象的思辨性的探索和生动、具体的诗歌形象紧密结合,并由此发展出一种“肉感中有思辨,抽象中有具体”、“形象和思想密不可分”(袁可嘉语)[袁可嘉. 诗人穆旦的位置[M].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15.]新的感性。诗人富于挑战性地采用一种思辨的方式来处理一个本属于激情的题材,把诗的感受力和思的洞察力熔铸为一体,并最终完成了新颖的诗情和独特而深入的思想的有机结合。
这种特殊的处理方式也决定了这首诗的语调的特殊性。组诗虽然袭用了普通情诗向恋人倾诉的口吻(这由诗中频繁出现的“你”一再向读者挑明),但我们在诗中却找不到对这一抒情对象的具体描绘,似乎她是没有脸甚至没有身体的(这和一般的情诗多么不同!)。因此,这个“你”在诗中的作用多少有一点像一件道具。也就是说,这首诗并不是为她而写:抒情主人公并不要求他的倾诉为对方听取。那么,它是为谁而写呢?在我看来,这组诗更多地是为抒情主人公自己而写。这样,诗的语调就由倾诉转化为一种内心独白。但是这样说也不完全确切,因为诗的语调并不完全是独白式的——除了表面的抒情对象,在这首诗的内部还有一个隐秘的倾听者和对话者。也正因此,它才能始终维持一种亲切的、节制的对话语气。实际上,这是一个作为观察者、审视者的“我”对另一个行动(爱的行动)的、存在的“我”所说的话——它那从容的、沉思的语调就由此产生。除此之外,这个语调还受到两个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量的牵扯,从而使其变得相当微妙。一个就是我们已经提到并贯穿全篇的“你”,另一个则是同样贯穿全篇的“上帝”。“我”——“你”——“上帝”三者的矛盾、冲突与亲和构成了推动诗篇进行的内在动力,也决定了诗歌语调的音域范围。此外,从这个基本的关系式中又推演出多重性质和重要性不太相同的关系,从而使诗篇的实际关系比上述简单的表述要复杂得多。诗中的“我”与“你”是第一重对应关系;“我”与 “你”结合而成为“我们”,并与“上帝”形成第二重对应关系;从“我”又分裂出一个源于“我”又对立于我的“他”(第六节),形成另一重对应关系;“你”身上又存在“年龄的小小野兽”和“理智的殿堂”的对立;“上帝”又以“火灾”、“重山”、“水流”、“黑暗”、“恐惧”、“那移动景物的”、“永青的巨树”等各种抽象的和具体的化身出场,更使诗中的关系之网变得如迷宫一般错综复杂。这种种关系之间的作用,“形成看不见的能量的网”[郑敏. 诗人与矛盾M].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39.],赋予了诗歌活跃的语流、呼吸和生命。身陷如此复杂的迷宫,没有阿里阿德涅的帮助,我们手无寸铁的诗人忒修斯怎样才能全身而退呢?对付这样的敌手,他既不能依靠锐利而快捷的行动之矛,也不能始终躲在情感的盾牌下,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他的智慧。他必须首先放慢脚步,调匀呼吸,然后虔诚地向他的雅典娜祷告,让智慧女神引导他穿越这个如此纷乱的存在的迷宫。事实上,在这首诗的进行中,思维一直持续地作用于语调,不断让语言减速,直到它适应思想的速度——最终把它从抒情的轨道扳转到思想的轨道上。
穆旦通过这首诗的语调为思想找到了一种声音表现的恰当方式。在这首诗中,诗歌凭借智慧穿越了存在的迷宫,忒修斯敏捷的身手和深湛的武功则由语调微妙的变化,灵巧的腾挪,突然的转向,令人惊叹的伸展、收缩,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意义的风吹拂着语调柔软的火焰,它的每一次轻盈的跳动、每一个美妙的姿态无不为这意义的风所塑造。声音和意义的关系在这里如此密切,仿佛身体和灵魂的精确、完美的结合。这一语调具有几个显著的特征:一是适应着思想运作的速度,节奏从容舒缓,音量也受到严格的控制——因为思想只能在沉寂中运转,稍微大一点的声音就会惊扰这位诗歌的娇客,而快捷的节奏反而会让思想的进行中断。与情感的直接反应和动作的进行相比,思维的运作显然更为迂回,速度也缓慢得多。思想的操练犹如蜘蛛的织网守侯猎物,需要绝对的耐心。事实上,一切创造的过程都势必要经历思维运转的艰难过程。二是回应着上述不同层次的关系,这个语调始终灵敏地、可靠地对速度、音调和音量做出精确的调整,呈现出微妙而层次丰富的变化。三是与思想上的怀疑倾向相联系,这一语调也呈现出矛盾的,自我否定的,犹豫不决,进退无定的特征。这样一种声音,由于它的复杂和微妙程度,几乎没有可能被还原为实际的人声。也就是说,这样的诗篇很难说是为人类的嗓音准备的,某种程度上,它是只为精敏的头脑准备的。但这并不是说,声音在这样的诗篇中不重要,恰恰相反,它的价值在这样的诗篇中得到了真正的体现。只是它那敏感而微妙的变化,使得只有一副绝对完美的嗓音——那意味着它有能力适应意义的任何细微变化而把这种变化呈现为实际的发声——才能将它毫无瑕疵地呈现出来;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人类发声器官。但是在阅读诗篇时,头脑却可以借助想象创造出一个这样的器官。也就是说,所谓纯粹为阅读准备的诗篇,并不是不要声音,而是对声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它表现出更加微妙的、细微的、层次丰富的效果。这样的声音效果,也许只有真正的音乐才能与之匹敌。这就是真正好的诗歌之所以对谱曲具有“抵抗性”的原因——因为它本身就是完成的音乐。读穆旦的这首诗,使我不由想起瓦莱里对马拉美《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的声音效果的赞叹:“我似乎见到了一种思想的形态首次被放置在我们的地面”[瓦莱里. 掷骰子的争论[M]. //瓦莱里散文选. 唐祖论,钱春绮,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19.]。马拉美那首诗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找到“一个精神工具来表达智力的和抽象想象的事物”,因而它具有“长期精确沉思经验的全部特征” [瓦莱里. 掷骰子的争论[M]. //瓦莱里散文选. 唐祖论,钱春绮,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24.]。穆旦这首诗在手段的应用(文学的和非文学的)上,没有走到马拉美那样的极端,但在表现“智力的和抽象想象的事物”的效果上却与马拉美那首诗有某种相类的地方。有意思的是,瓦莱里在听了马拉美本人朗诵“骰子”一诗以后,对职业朗诵家的“朗诵艺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人类声音的内部是这样的美,以至我几乎永远都接受不了那些职业的朗诵家。当他们的意愿超载泛滥时,他们自以为强调得体、演绎得当;当他们用自己的抒情来代替单字组成的诗歌时,他们就败坏了一部作品的和谐。他们的职业以及他们自相矛盾的技艺,难道不是使听众在短暂之间把最漫不经心的诗歌当成最崇高的诗歌,然而他们却使大部分依靠自身价值而存在的作品变得可笑,趋于毁灭?” [瓦莱里. 掷骰子的争论[M]. //瓦莱里散文选. 唐祖论,钱春绮,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19.]穆旦这首诗同样是那种只能由人类“内部的声音”来处理的诗歌,任何外在的朗诵技巧都将败坏它那纯粹的品质。
我们说穆旦这首诗的语调体现了思想运作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摒弃了情感的因素或者缺少感性的魅力。穆旦诗歌的特异之处就在于它“肉感中有思辨,抽象中有具体”,“形象和思想密不可分”的特征。可以说,穆旦始终恪守“用身体思想”的训诫。在他那些优秀的诗篇中,情感获得了思想的深度,思想则拥有着感性的魅力。对这首诗来说同样如此。这首诗是对爱情的玄学沉思,但这个沉思仍然是以情感的体验为基础的。甚而言之,正是因为抒情主人公的情感太热烈、太一往情深了,才需要用玄学的思辨加以节制,从而摒弃那种陈腐的、滥情而不加节制的表达方式。换句话说,穆旦并不是摒弃情感,而是将情感思想化了。如果我们认真对自己心灵的历史进行一番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只有一种顽强的、深入而持久的情感才能在时间的作用下获得思想的形状。这一作用的机理类似于卞之琳吟咏的“水成岩”:“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积下了层叠的悲哀”。[袁可嘉. 诗人穆旦的位置M].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15.]诗歌中有价值的思想说到底还是一种情感的积淀——它是情感的化石,看见它就能唤起我们对于情感的色、香、味以及它的热度的鲜明的记忆。
穆旦诗歌复杂的语调,真实地反映了穆旦对现代境遇下人的意识的复杂状态的体味和认知。这种复杂性在他的诗中进一步表现为其“自我”形象的不确定性。香港诗人梁秉钧认为,穆旦诗歌中的自我是矛盾的、分裂的、破碎的,既虚幻又不可保持;这与此前新诗中对一个稳定的、统一完整的、无可争辩的“自我”的确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梁秉钧对穆旦《诗八首》第二首诗中的“自我”形象做过这样的分析:“这诗里有不少矛盾,你我既沉淀又成长,既死又生(子宫),既有无数可能又永远不能完成自己,既相信相爱又有暗笑,既有你我又有另外的你我,我们既丰富又危险。诗里有不少矛盾,但我们不觉得这仅是‘矛盾语法’的技巧或是机智的卖弄,为什么呢?大概就是因为诗里对‘自我’有一种比较复杂而深刻的认识,令我们觉得那些矛盾,不仅存在于文字,是从对人的体会里来的。诗里对‘自我’的看法是:自我不是固定不变,是会变更,会转化的。”[梁秉钧. 穆旦与现代的我[M].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51. 我个人认为,梁秉钧的这篇论文显然是穆旦研究中分量最重的批评文章之一。]这段话对一些具体的词句和意象的分析未必确当,但却抓住了穆旦诗歌中一个根本性的东西,那就是破除了新诗人长期以来存在的对“自我”的迷信。实际上,穆旦这首诗中的自我不单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是分裂的。第六首说,“他存在,听从我底指使,/他保护,而把我留在孤独里,/他底痛苦是不断的寻求/你底秩序,求得了又必须背离”。我们在上文中曾经分析过,这个“他”实际上是从“自我”中分裂出来的。“自我”一方面服从于自然的秩序,“存在”、“保护”并“不断的寻求”,另一方面却又分裂出一个观察者,对这“存在”和“保护”和“寻求”的行动进行观察和反思。在这样的观察和反思里,观察者发现的是奇异的矛盾:“保护”的结果是“把我留在孤独里”(“保护”意味着对“自我”的持守,同时意味着对外在世界的拒绝);“不断的寻求”的结果反而是“背离”。这样,在行动的“自我”和观察的“自我”之间就产生了“反讽的距离”。行动和结果的这种矛盾,否定了自我的统一性,也使第一行中提出的“他存在,听从我底指使”这一肯定的结论失去了依据。在这短短的四行诗里,诗思演绎的结果是否定了自身的出发点。正是通过这种在肯定和否定之间的不断的试探、迂回、前进、转身和回刺,诗歌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拓展。
穆旦诗中这个思想者的声音在新诗历史上是罕见的,它也许只在冯至、卞之琳的诗中短暂地闪现过。此前新诗中具有典型意义的语调包括郭沫若的戏剧朗诵语调、戴望舒的说话语调、艾青界于朗诵和说话之间而偏于朗诵的语调。这几种语调的节奏模式都是情感性的,也都可以用实际的人类发声加以重现。在一个好的朗诵者那里,他们的诗歌声音的魅力不会被削弱,甚至可以借助朗诵者熟练的技巧和动听的嗓音而得到加强。而像穆旦《诗八首》这样的诗,是在人类嗓音的表现力之外的。它在声音和意义之间形成了更为密切的结合,两者之间更加贴合无间。卞之琳、冯至虽然也都进行了让思想声音化的努力,但在他们那里,这一努力还都没有达到自如的程度。在他们的诗中,思想和声音之间还不能达到完全和谐一致,常常互相掣肘,有时是声音妨碍了思想的运行,有时则是思想的运行妨碍了语流的顺畅;这些在穆旦的诗中都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克服。从这个意义上讲,穆旦这组诗无疑也表现出了一种卓异的品格。

